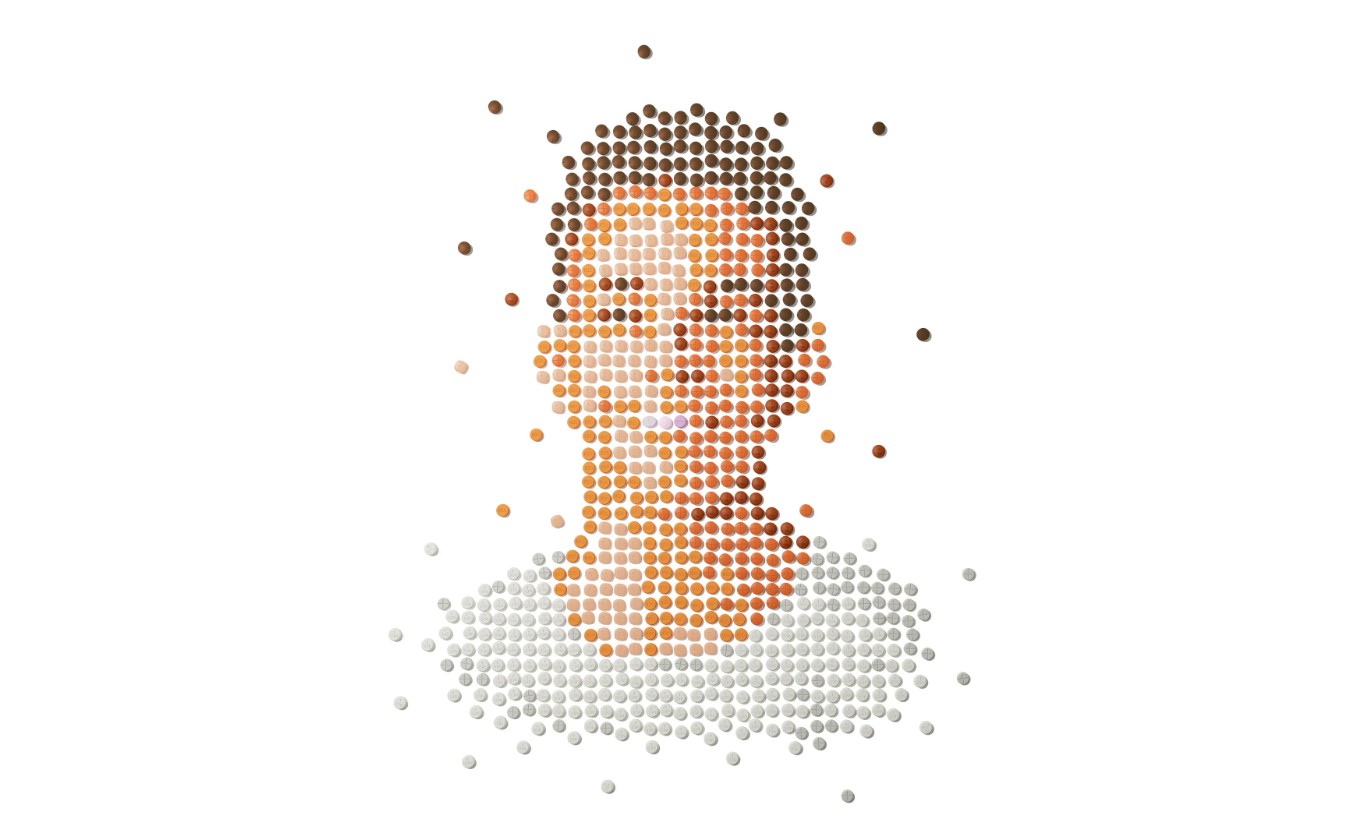診斷病例達到歷史新高,一些專家開始質疑我們對這種狀況的假設——以及如何治療它。
作者:Paul Tough Paul Tough 是該雜誌的特約撰稿人,在過去二十年,他撰寫了關於教育和兒童發展的文章和書籍。
2025 年 4 月 13 日 在 1990 年代初,James Swanson 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擔任研究心理學家,他專門研究注意力障礙。那是該領域一個敏感的時期。山達基教會(Church of Scientology)發起了一場全國性的抗議運動,反對精神醫學專業,而 Ritalin ——當時處方給診斷為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的兒童的主要藥物——是其主要目標之一。每當 Swanson 和他的同事們聚集參加科學會議時,他們都會遇到高呼口號的抗議者揮舞標語,以及頭頂飛機拖著橫幅,上面寫著:「Psychs, Stop Drugging Our Kids.」(精神科醫生,停止給我們的孩子下藥。)
的確,Ritalin 的處方率正在上升。1990 年代初,美國被診斷為 A.D.H.D. 的兒童數量增加了一倍多,從 1990 年的不到一百萬名患者增加到 1993 年的超過兩百萬名,其中幾乎三分之二被處方 Ritalin。對當時的 Swanson 來說,這種增加似乎完全合適。這兩百萬兒童佔全國兒童人口的約 3%,而 3% 是他和許多其他科學家認為兒童中 A.D.H.D. 的準確發生率。
儘管如此,你不必是 Scientologist(山達基信徒)才能承認 A.D.H.D. 存在一些合理的疑問。儘管 Ritalin 的快速增長,沒有人確切知道這種藥物是如何起作用的,或者它是否真的是治療兒童注意力問題的最佳方式。從軼事來看,醫生和父母會觀察到,當許多兒童開始服用像 Ritalin 這樣的興奮劑藥物時,他們的行為幾乎一夜之間就會改善,但沒有人在一個仔細、大規模的科學研究中測量這種正面反應有多常見,或者說,長期服用 Ritalin 對兒童的影響是什麼。因此,Swanson 和一組研究人員,在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資助下,開始了一項龐大的、多點隨機對照試驗(multisit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比較 A.D.H.D. 的興奮劑治療與非藥物方法,如父母訓練和行為指導。
Swanson 負責加州橘郡(Orange County, Calif.)的試驗點。他招募並選出了約 100 名有 A.D.H.D. 症狀的兒童,全都 7 到 9 歲。他們被分為治療組——有些給予定期劑量的 Ritalin,有些給予高品質的行為訓練,有些給予組合,而其餘的,對照組,則被留下來自己找出他們的治療方法。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大陸上的其他五個試驗點。被稱為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的多模式治療研究(Multimodal Treatment of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Study),或 M.T.A.,這是曾經進行的任何精神藥物長期影響的最大研究之一。
「我們對 A.D.H.D. 的臨床定義,正越來越 unanchored(脫離錨定)於我們在科學中發現的東西。」
M.T.A. 研究的初步結果,於 1999 年發表,強調了興奮劑藥物的論據。在治療 14 個月後,每天服用 Ritalin 的兒童症狀明顯比只接受行為訓練的兒童少。消息傳遍全國的診所和兒科醫生辦公室:Ritalin 有效。這不僅對有注意力問題兒童的家庭是好消息,也對提供藥物解決方案的公司是好消息。在研究初步發表後的幾年,Swanson 開始為製藥公司提供諮詢。他建議製造 Adderall ——一種類似的興奮劑藥物——的 Shire,如何配製其產品的緩釋版(extended-release),以便兒童每天早上只需服用一顆藥丸,而不必在一天中途去學校護士辦公室。
雖然 Swanson 歡迎診斷率的初步增加,但他預期它會在 3% 平穩下來。相反,它持續上升,在 1997 年達到美國兒童的 5.5%,然後在 2000 年達到 6.6%。隨著時間推移,Swanson 開始感到不安。他和他的同事們繼續追蹤 M.T.A. 研究中近 600 名兒童,到 2000 年代中期,他們意識到他們收集的新數據講述了一個不同——且較不樂觀——的故事,比他們最初報告的要不同。治療 14 個月後,服用 Ritalin 的兒童行為確實比其他組更好。但到 36 個月時,這種優勢完全消失,每一組的兒童,包括對照組,都顯示出完全相同的症狀水平。Swanson 現在 80 歲,接近職業生涯的尾聲,當他談論自己一生的工作時,他聽起來很困擾——不僅是關於 M.T.A. 結果,還關於 A.D.H.D. 領域的整體狀態。「我們做這項工作的某些方式,」他告訴我,「絕對是錯的。」
過去一年,我與美國和海外一些領先的 A.D.H.D. 研究人員交談,其中許多人,像 Swanson 一樣,對他們所看到的現象表達擔憂:新興的科學理解與 A.D.H.D. 在診所和醫生辦公室的治療方式之間存在 disconnect(斷裂)。Edmund Sonuga-Barke 是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精神醫學和神經科學研究人員,他以個人角度描述了這種情況。「我投入了 35 年的人生試圖找出 A.D.H.D. 的原因,不知何故,我們似乎比開始時離目標更遠了,」他告訴我。「我們對 A.D.H.D. 的臨床定義,正越來越 unanchored(脫離錨定)於我們在科學中發現的東西。」
儘管這些科學家開始提出疑問,但診斷的增長並沒有顯示出停止或甚至放緩的跡象。去年,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報告稱,11.4% 的美國兒童被診斷為 A.D.H.D.,創下歷史新高。這個數字包括 15.5% 的美國青少年、21% 的 14 歲男孩和 23% 的 17 歲男孩。七百萬美國兒童獲得 A.D.H.D. 診斷,高於 2016 年的六百萬和 1990 年代中期的兩百萬。
A.D.H.D. 的首選治療仍然是興奮劑藥物,包括 Ritalin 和 Adderall,而這些興奮劑的市場在近年來迅速擴張,與診斷的增長同步。從 2012 年到 2022 年,用於治療 A.D.H.D. 的興奮劑處方總數在美國增加了 58%。雖然處方率最高的是 10 到 14 歲的男孩,但如今興奮劑藥物的真正增長市場是成人。2012 年,30 多歲的美國人獲得了五百萬張用於治療 A.D.H.D. 的興奮劑處方;十年後,這個數字增加了三倍多,上升到一千八百萬。
那座不斷擴大的藥丸山堆基於某些假設:A.D.H.D. 是一種需要醫療解決方案的醫療障礙;它是兒童大腦固有缺陷造成的;我們給他們的藥物修復了這些缺陷。研究 A.D.H.D. 的科學家現在正在挑戰每一個這些假設——並發現兒童環境在症狀進展中作用的新證據。他們不質疑導致家庭尋求 A.D.H.D. 治療的真正問題,但許多人相信我們目前的做法沒有足夠幫助——而且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但首先,他們說,我們需要重新思考許多關於這種障礙的舊觀念,並開始 anew(重新)看待 A.D.H.D.。
A.D.H.D. 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診斷。懷疑者主張,這種障礙的許多經典症狀——fidgeting(坐立不安)、丟東西、不遵從指示——只是兒童典型的、雖然煩人、行為。作為回應,其他人指出,當這些症狀變得更嚴重時,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包括學業失敗、社會排斥和嚴重的情緒困擾。
那麼,你該如何劃線?如何分辨一個正常活潑的孩子和有 A.D.H.D. 的兒童?臨床醫生用來做出這種區分的工具是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或 D.S.M.,它提供了一份症狀清單,用來診斷患者,包括九個潛在的 inattention(注意力不集中)症狀和九個 hyperactivity/impulsivity(過動/衝動)症狀。要符合診斷,一個兒童必須顯示來自任一類別的六個症狀,具有足夠的嚴重度和損害水平,至少持續六個月,從 12 歲前開始,而且這些症狀必須出現在兩個不同的情境(如家裡和學校)。
這似乎相當科學——六個症狀、兩個情境、六個月、12 歲——它反映了該領域許多人長期努力,將 A.D.H.D. 描繪成一種有明確診斷界限的 straightforward(直截了當的)醫療狀況。Russell Barkley 是最著名的 A.D.H.D. 研究人員之一,他將這種障礙標記為「大腦的糖尿病」(diabetes of the brain),並在 YouTube 上觀看次數超過四百萬次的演講中,他說,就像糖尿病一樣,A.D.H.D. 是「一種慢性障礙,必須每天管理,以防止它將造成的次要傷害。」在最近一篇 ADDitude ——一本受家庭和患者歡迎的流行雜誌——的文章中,Wes Crenshaw ——一位被列為該雜誌醫療審查小組成員的心理學家——更 sharply(尖銳地)劃定了 A.D.H.D. 的邊界。「你的孩子要麼有 A.D.H.D.,要麼沒有,」Crenshaw 寫道。「如果他有,他要麼受損,要麼不受損。如果他受損,談話療法或補充劑或營養或運動或紀律都不會解決那個。」
然而,現在,一些科學家開始主張,將 A.D.H.D. 傳統觀念視為關於你的不變、本質事實——某種你 simply have or don’t have(單純有或沒有)、某種 wired deep in your brain(深植大腦)的東西——既 inaccurate(不準確)也不 unhelpful(無幫助)。根據英國研究人員 Sonuga-Barke 的說法,傳統觀念認為存在一個「有 A.D.H.D. 的人」的自然類別,臨床醫生可以客觀測量和定義,「just doesn’t seem to be the case.」(似乎並非如此。)
準確診斷 A.D.H.D. 可能具有挑戰性,原因有很多。與糖尿病不同,A.D.H.D. 沒有可靠的生物測試。D.S.M. 中的診斷標準往往需要主觀判斷,而且歷史上這些標準相當 fluid(流動),隨著手冊的每次修訂而變化。診斷涵蓋了廣泛的行為。有兩種主要的 A.D.H.D. 類型,inattentive(注意力不集中型)和 hyperactive/impulsive(過動/衝動型),一類中的兒童往往似乎與另一類中的兒童沒有多少共同點。有 A.D.H.D. 的人,有些你無法讓他們停止說話,其他人你無法讓他們開始。有些過度 eager(熱切)和 enthusiastic(熱情);其他人則 irritable(易怒)和 moody(情緒化)。
A.D.H.D. 在 D.S.M. 中被定義為一種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神經發育障礙),但 A.D.H.D. 的症狀也可以由各種環境原因產生。難以坐定和維持注意力也可以是嚴重頭部損傷、fetal alcohol syndrome(胎兒酒精症候群)、兒童鉛暴露、早期創傷等的症狀。A.D.H.D. 的症狀與其他精神障礙的症狀之間也有高度重疊,包括 depression(憂鬱)、anxiety(焦慮)、dyslexia(閱讀障礙)和 autism(自閉症)。雖然 D.S.M. 指定,如果兒童的症狀更好地由另一種精神障礙解釋,臨床醫生不應診斷為 A.D.H.D.,但根據 C.D.C.,診斷為 A.D.H.D. 的兒童中,超過四分之三同時有另一種 mental-health condition(心理健康狀況)。chadd.org超過三分之一有 anxiety 診斷,一個類似比例有診斷的 learning disorder(學習障礙)。44% 被診斷為像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對立性反抗障礙)這樣的行為障礙。
這一切都使將 A.D.H.D. 描繪成一種 distinct(獨特的)、unique(獨特的) biological disorder(生物障礙)的努力變得複雜。一個有六個症狀的患者真的與有五個症狀的患者有那麼大不同嗎?如果一個經歷早期創傷的孩子現在無法坐定或保持井井有條,她應該被治療為 A.D.H.D. 嗎?一個有 anxiety disorder(焦慮障礙)的孩子不斷被她的擔憂分散注意力呢?她是有 A.D.H.D.,還是只是由她的 anxiety(焦慮)引起的類似 A.D.H.D. 的症狀?
為了試圖 clarify(澄清)和 better define(更好地定義) A.D.H.D. 的邊界,研究人員長期以來一直尋求識別這種障礙的 biological signature(生物標誌),或「biomarker」(生物標記)——一種 clear test(明確測試),就像糖尿病 的 blood-glucose test(血糖測試),讓臨床醫生能夠確切說出哪些兒童有 A.D.H.D.,哪些沒有。而在 21 世紀初,似乎他們即將成功。
2002 年,Russell Barkley ——當時是麻省大學醫學院(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edical School)精神醫學和神經學教授,也是幾本關於 A.D.H.D. 的流行書籍的作者——起草了一份「international consensus statement」(國際共識聲明),由 85 位著名研究人員簽署,捍衛 A.D.H.D. 診斷的有效性。它 heavily(嚴重地)依賴早期的研究,這些研究表明確實存在這種障礙的 solid biomarkers(堅實生物標記),例如主張,有 A.D.H.D. 的人在某些腦區有「less brain electrical activity」(較少的大腦電活動)比沒有診斷的人;已經發現一個 single gene(單一基因)與這種障礙相關;以及診斷為 A.D.H.D. 的人有「relatively smaller areas of brain matter」(相對較小的腦物質區域)。
然而,在共識聲明發表後的這些年,每一個這些 A.D.H.D. biomarkers 的證據都 faltered(動搖)。試圖 replicate(複製)顯示腦電活動差異的研究的嘗試 came up empty(一無所獲)。雖然科學家已經識別出複雜的基因集合,這些基因一起可能表示 A.D.H.D. 的更大風險,但他們未能找到一個 specific gene(特定基因)來預測這種障礙。「There is no single-gene story」(沒有單一基因的故事),麻省理工學院(M.I.T.)神經科學家 John Gabrieli 最近告訴我。「十五年前,有 incredible optimism(難以置信的樂觀),現在我們意識到我們有多遠。」
「字面上,沒有自然的 cutting point(切割點),你可以說,『這個人有 A.D.H.D.,這個人沒有。』」
尋找 A.D.H.D. biomarker(生物標記)的最 ambitious(雄心勃勃的)努力是由 Enigma Consortium(Enigma 聯盟)進行的,這是一個全球科學家網絡,分享來自超過 4,000 名受試者的腦掃描數據。早期的研究發現了診斷為 A.D.H.D. 患者的腦部物理差異的 indications(跡象)——Barkley 聲明中的「relatively smaller areas of brain matter」(相對較小的腦物質區域)。但是,當由荷蘭神經科學家 Martine Hoogman 領導的團隊花費數年比較 Enigma 受試者診斷為 A.D.H.D. 的「cortical volumes」(皮質體積)與對照組時,結果再次 disappointing(令人失望)。在成人和青少年中,兩組之間完全沒有差異;在兒童中,差異如此 minor(微小)以至於 almost imperceptible(幾乎察覺不到)。正如 Edmund Sonuga-Barke 告訴我的,「Enigma 顯示的是,我們認為存在的東西其實不存在。」
令許多人驚訝的是,當 Hoogman 和她的團隊在 2017 年發表他們的結果時,他們聲稱數據事實上顯示了 opposite(相反),conclusively(決定性地) demonstrating(證明) A.D.H.D. 的 biological nature(生物本質):「我們用 high-powered analysis(高功率分析)確認,A.D.H.D. 患者有 altered brains(改變的大腦);因此 A.D.H.D. 是一種大腦障礙,」研究人員寫道。「這個訊息對臨床醫生傳達給父母和患者很 clear(清楚),這有助於 reduce the stigma(減少汙名) of A.D.H.D. 並 improve understanding(改善理解) of the disorder。」
當我最近透過電子郵件採訪 Hoogman 時,我驚訝地得知,她現在希望能夠 revise(修訂)那個聲明。「當時,我們 emphasized(強調)我們發現的差異(雖然 small(小)),但你也可以 conclude(結論) A.D.H.D. 的人和沒有 A.D.H.D. 的人的 subcortical(皮質下)和 cortical volumes(皮質體積) almost identical(幾乎相同),」她寫道。回顧起來,她補充說,從她的發現 conclude(結論) A.D.H.D. 是一種腦障礙並不 fitting(合適)。「A.D.H.D. 的 neurobiology(神經生物學)比那複雜得多。」
Sonuga-Barke 更 further(進一步),主張整個數十年尋找 biomarker 的 quest(追求)對該領域來說是「a red herring」(紅鯡魚/誤導)。他理解他的同事們渴望找到 A.D.H.D. biological nature(生物本質)的 airtight evidence(嚴密證據),這可以幫助他們 defend the diagnosis(捍衛診斷)對抗那些會完全 dismiss(駁斥)它的人。「在該領域,我們如此 frightened(害怕)人們會說它不存在,」他說。「這只是 bad parenting(不良教養),從右派來看,或這只是我們 postindustrial society(後工業社會)的產物,從左派來看。我們必須 double down(加倍努力)因為我們 terrified(恐懼)那些無法得到 meds(藥物)的孩子會發生什麼。我們已經看到它們對人們生活的 impact(影響)。」
但現實情況,他說,是「字面上,沒有自然的 cutting point(切割點),你可以說,『這個人有 A.D.H.D.,這個人沒有。』那些決定在某種程度上是 arbitrary(任意的)。這並不意味著與 A.D.H.D. 相關的 suffering(痛苦)是 imaginary(想像的),它只是意味著它在一個 continuum(連續體)上。那就是 A.D.H.D. 的 conundrum(難題)——empirical crisis(經驗危機)。」
未能找到明確的 biomarker(生物標記)並不意味著 A.D.H.D. 沒有 biological basis(生物基礎);我交談的大多數科學家同意,這種狀況是由 biological(生物)和 environmental forces(環境力量)的某種組合產生的,雖然關於每種的相對重要性幾乎沒有 consensus(共識)。但這對該領域確實有某些 implications(含義),包括對藥物問題。如果我們不再 confident(確信) A.D.H.D. 有 purely biological basis(純粹生物基礎),那麼我們 go-to treatment(首選治療)仍然 rooted in biology(根植於生物學)還有意義嗎?
當前治療模式的 roots(根源)可以追溯到 1937 年,當時一位哈佛訓練的精神科醫生名為 Charles Bradley 在他命名 dramatic(戲劇性)的《美國瘋狂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Insanity)中發表了他在羅德島東普羅維登斯(East Providence, R.I.)為有行為問題兒童經營的診所進行的實驗結果。一週內,Bradley 給他的 30 名年輕患者每天一劑 benzedrine(苯丙胺),這是一種當時在爵士音樂家和大學生中流行的安非他命。十四名兒童以 Bradley 描述為「a spectacular fashion」(壯觀的方式)回應。從他們第一劑的日子起,他們的老師報告「remarkably improved school performance」(顯著改善的學校表現)。一夜之間,學生們似乎第一次對他們的學業感興趣。他們變得更「placid and easygoing」(平靜且隨和),他們自發地對老師說像「I feel fine and can’t seem to do things fast enough today」(我感覺很好,今天似乎做事情快不夠)和「I start to make my bed, and before I know it, it is done」(我開始整理床鋪,不知不覺就完成了)這樣的評論。
近九十年後,A.D.H.D. 的治療並沒有超出 Bradley 的發現太多。現在這種障礙的 leading treatment(主要治療) Adderall 是一種 amphetamine(安非他命),就像 Bradley 給他的患者服用的 benzedrine 藥丸;其他 leading prescription stimulants(主要處方興奮劑),包括 Ritalin,都是同一化學化合物的 variations(變異)。
「在行為上的 almost awesome effects(幾乎令人驚嘆的效果)和在 academic achievement or attainment(學業成就或獲得)上的 minimal effects(最小效果)之間,有一個 real disconnect(真正的斷裂)。」
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的神經科學研究人員 F. Xavier Castellanos 偶爾會回頭閱讀 Bradley 的原論文,他告訴我,今天,當他的 A.D.H.D. 患者第一次服用興奮劑藥物時,他經常看到 Bradley 在 1930 年代觀察到的相同效果。「第一劑幾乎像是一種 mystical experience(神秘體驗),」Castellanos 說。「你會看到這種 transformation(轉變)。行為上的益處真的有點 stunning(驚人),尤其是在年輕孩子身上。」
但就像幫助領導 M.T.A. 研究的 James Swanson 一樣,Castellanos 對 A.D.H.D. 的興奮劑治療有一些 real concerns(真正的擔憂)。他說他對研究中一個 persistent finding(持續發現)感到 frustrated(沮喪):雖然這些藥物對兒童在教室中的行為有 powerful effect(強大效果),但它們對他們的學習改善卻 little(很少)。「這是一個 puzzle(謎團),」Castellanos 說。「在行為上的 almost awesome effects(幾乎令人驚嘆的效果)和在 academic achievement or attainment(學業成就或獲得)上的 minimal effects(最小效果)之間,有一個 real disconnect(真正的斷裂)。讓我困擾的是,孩子們做更多 seatwork(座位作業)——你可以看到他們做了更多問題——但當你在一兩週後測試他們時,他們的分數 barely budge(幾乎不動)。或者完全不動。那就是真正讓我 frustrated(沮喪)的事情。」
這種效果在多年來的許多研究中出現,但有兩個相對 recent(最近)的例子很好地 illustrate(說明)它。一個是由澳洲神經科學家 Elizabeth Bowman 和英國精神科醫生 David Coghill 於 2023 年發表。他們在澳洲招募了 40 名年輕成人,給其中一些人興奮劑 A.D.H.D. 藥物,其他人 placebo(安慰劑),然後讓他們解決一系列稱為 knapsack-optimization problems(背包優化問題)的 complex tests(複雜測試)。Knapsack problems(背包問題)是經濟學和電腦科學中著名的 puzzles(謎題)。你被給予一個虛擬背包和一系列不同重量和價格的物品,你需要找出物品的 assortment(組合),以 maximize(最大化)你的負載的 dollar value(美元價值)。
被給予興奮劑的受試者比服用 placebo(安慰劑)的人工作得更 quickly(快速)和 intensely(強烈)。他們 dutifully(盡責地) packed and repacked(打包和重新打包)他們的虛擬背包,pulling items in and out(把物品拉進拉出),試圖 various combinations(各種組合)。然而,最終,他們在 knapsack test(背包測試)上的分數 no better(不比) placebo group(安慰劑組)好。原因?他們選擇物品的 strategies(策略)在藥物下變得 significantly worse(顯著更糟)。他們的選擇 didn’t make much sense(沒有太多意義)——他們只是 kept pulling random items in and out of the backpack(不斷把隨機物品拉進拉出背包)。對觀察者來說,他們 appear(顯得) focused(專注)、well behaved(行為良好)、on task(專注任務)。但事實上,他們 weren’t accomplishing anything of much value(沒有完成任何有太多價值的東西)。
一位名為 William Pelham Jr. 的佛羅里達研究人員在 2022 年發表的研究中發現了 similar(類似)的東西。與澳洲研究不同,這一個涉及的不是成人,而是 7 到 12 歲的兒童,全都參加為 A.D.H.D. 兒童設計的八週 summer camp(夏令營)。他們的日子分為 classroom learning(教室學習)和 regular camp activities(常規營隊活動)。Pelham 和他的同事們 randomly(隨機)將兒童分為 treatment group(治療組)和 control group(對照組)。治療組得到 Ritalin 的 active ingredient(活性成分)的 regular daily dose(定期每日劑量),對照組被給予 placebo(安慰劑)。
與澳洲研究一樣,服用 Ritalin 的兒童在教室中工作得更快、行為更好,比 placebo group(安慰劑組)更好。但再次,他們並沒有比 control group(對照組)學習到更多。「雖然數十年來一直相信,藥物對學業座位作業生產力和教室行為的效果會 translate(轉化)成改善新學業材料的學習,」科學家們寫道,「我們沒有發現這樣的 translation(轉化)。」
那麼,這是怎麼回事?如果這些研究是 accurate(準確的),興奮劑藥物對改善 cognitive ability(認知能力)或 academic performance(學業表現)並沒有多大作用。然而,數百萬年輕美國人(和他們的父母)覺得這些藥丸對他們在學校的成功是 essential(必要的)。為什麼?
一個 possible explanation(可能的解釋)可以在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 cognitive neuroscientist(認知神經科學家) Martha Farah 的工作中找到。在一項研究中,她和一位同事 Irena Ilieva 招募了 46 名年輕成人,給其中一半一劑 Adderall,另一半 placebo(安慰劑),然後讓他們進行 13 種不同的 cognitive tests(認知測試)。服用藥物的人在任何測試中都沒有比服用 placebo(安慰劑)的人做得更好,但當研究人員要求受試者 evaluate(評估)他們在 assessments(評估)中的 performance(表現)時,服用 Adderall 的人相信他們做得更好。他們感覺更 confident(自信),即使他們的 actual abilities(實際能力)並沒有改善。
Farah 引導我去看 Scott Vrecko 的工作,他是一位 sociologist(社會學家),對美國一所大學中使用無處方興奮劑藥物的學生進行了一系列 interviews(訪談)。他寫道,他訪談的學生經常「frame the functional benefits of stimulants in cognitive-sounding terms」(以聽起來像認知的術語來框定興奮劑的功能益處)。但當他 dug a little deeper(挖掘得更深)時,他發現學生傾向於以 emotional terms(情緒術語)而不是 intellectual ones(智力術語)來談論他們的注意力掙扎,以及他們在藥物下體驗到的益處。沒有藥丸,他們說,他們只是對他們應該做的 assignments(作業)不感到 interested(感興趣)。他們不感到 motivated(有動機)。一切似乎 pointless(無意義)。
在興奮劑藥物下,那些情緒 flipped(翻轉)。「你開始感覺到與你正在做的事情有這樣的 connection(連接),」一位大學生告訴 Vrecko。「It’s almost like you fall in love with it.」(這幾乎就像你愛上它一樣。)正如另一位學生所說:在 Adderall 上,「you’re interested in what you’re doing, even if it’s boring.」(你對你正在做的事情感興趣,即使它是無聊的。)
歷史上,這是人們服用 amphetamines(安非他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們讓 tedious tasks(乏味任務)似乎更有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軍方分發了數千萬片 amphetamine tablets(安非他命藥片)給士兵,用於戰爭中許多 boring stretches(無聊時期)。這些藥丸給予執行 long missions(長途任務)的空軍飛行員,以及必須整夜 keep watch(守夜)的海軍水手。在 1950 年代,郊區家庭主婦服用 amphetamines 來度過無盡的 housework(家務)和 child care(兒童照顧)的 boredom(無聊)。長途卡車司機數十年來使用它們來 tolerate(忍受) the tedium of the road(道路的單調)。對於 Scott Vrecko 訪談的大學生來說,term papers(學期論文)就像 laundry(洗衣)或 long-haul truck route(長途卡車路線)一樣無聊——但在 stimulants(興奮劑)的幫助下,它們變得更 bearable(可忍受)。
「There is no long-term effect. The only long-term effect that I know of has been the suppression of growth.」(沒有長期效果。我所知道的唯一長期效果是生長抑制。)
原來的 M.T.A. 研究,就像後來的 knapsack-problem study(背包問題研究)和 summer-camp study(夏令營研究),顯示了興奮劑藥物對行為的 strong effect(強大效果)和對 academic achievement(學業成就)幾乎 no impact(沒有影響)。回到 2000 年代初,Swanson 對那些結果感到 troubled(困擾),但對他來說,更大的 issue(問題)是,即使在興奮劑下的 behavioral benefits(行為益處) faded out(消退)得如此 completely(完全)。他和他的同事們在那十年花費了大部分時間 analyzing and reanalyzing(分析和重新分析) M.T.A. 數據,他們不斷得到相同的結果:在治療的第一年後,Ritalin 對行為的 relative positive effects(相對正面效果)開始 shrink(縮小),到第三年結束時,它們已經 disappeared altogether(完全消失)。
他們在數據中注意到另一個 distressing result(令人不安的結果)——一個 physiological(生理的)結果。長期服用 Ritalin 的兒童比 nonmedicated(未服藥)的兒童生長得更慢。到那 36 個月結束時,一貫服用興奮劑藥物的受試者平均比從未接受藥物的受試者 short(矮)超過一英寸。M.T.A. 組的許多科學家 assumed(假設)這種 childhood(兒童期)的 height suppression(身高抑制)是 temporary(暫時的)——那些 shorter children(較矮的兒童)會在 adolescence(青春期) catch up(趕上)——但當初始實驗九年後再次收集數據時,height gap(身高差距) remained(仍然存在)。在 2017 年,Swanson 和 M.T.A. 組發表了另一個 follow-up(追蹤),這次追蹤受試者到 25 歲。一貫服用興奮劑藥物的人 remained about an inch shorter than their peers(比他們的同齡人矮約一英寸)。與此同時,他們的 A.D.H.D. 症狀 no better(不比)那些已經停止服用藥物或從未開始的人好。
研究人員 acknowledge(承認)服用 prescription stimulants(處方興奮劑)有其他 inherent risks(固有風險)。Amphetamines 可以 powerfully addictive(強烈成癮),去年,在《美國精神醫學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的一項研究發現,即使是 medium-strength(中等強度) daily dose(每日劑量)的 Adderall 也會 more than tripled(增加三倍以上)患者發展 psychosis(精神病)或 mania(躁狂)的 likelihood(可能性)。psychiatryonline.org高劑量將風險 increased by a factor of five(增加五倍)。儘管如此,對大多數科學家,包括 Castellanos、Sonuga-Barke 和 Gabrieli,藥物的 positives(正面) outweigh the negatives(勝過負面)。正如 Gabrieli 所說,「I feel the bigger risk is people not getting help who are struggling in everyday life.」(我覺得更大的風險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掙扎的人沒有得到幫助。)
與其他 psychiatric medications(精神藥物)相比,Gabrieli 解釋說,Ritalin 和 Adderall(以及今天市場上許多 similar formulations(類似配方))相對 safe(安全)和 effective(有效)。它們並不幫助每個人,但至少在 short term(短期),它們為大多數服用它們的兒童提供 significant symptom control(顯著症狀控制)。臨床醫生一般認為它們 easy to prescribe(容易處方),部分原因是它們通常對患者 easy to quit(容易停止)。不像 antidepressants(抗憂鬱藥)或許多 anti-anxiety medications(抗焦慮藥),它們不會在 bloodstream(血流)中 linger(停留)超過一天,這意味著即使是 extended-release versions(緩釋版),它們也不需要 weaning process(漸停過程)。你可以 just stop taking them(直接停止服用)。「At some level」(在某種程度上),Gabrieli 告訴我,「these stimulants are not that far from Red Bull.」(這些興奮劑與紅牛飲料沒有那麼大的差別。)
在研究 stimulants(興奮劑)三十年後,Swanson 在它們的 value(價值)上與許多同事 differs(不同)。「I don’t agree with people who say that stimulant treatment is good」(我不同意那些說興奮劑治療是好的的人),他告訴我。「It’s not good.」(它不好。)他 acknowledges(承認)藥物往往可以產生兒童行為的 short-term improvements(短期改善)。但是,他說,「there is no long-term effect. The only long-term effect that I know of has been the suppression of growth. If you’re honest, you should tell kids that, look, if you’re interested in next week or next month or even the next year, this is the right treatment for you. But in the long run, you’re going to be shorter. How many kids would agree to take medication? Probably none.」(沒有長期效果。我所知道的唯一長期效果是生長抑制。如果你誠實,你應該告訴孩子們,看,如果你對下週或下個月甚至下一年感興趣,這是適合你的治療。但從長遠來看,你會變得更矮。有多少孩子會同意服用藥物?可能沒有。)
當我和全國各地的學生談論他們對 A.D.H.D. 藥物的 experiences(經驗)時,他們與 stimulants(興奮劑)的 relationship(關係)往往 turned out to be quite complex(相當複雜)。Cap,一位東海岸郊區的青少年,告訴我,他在高中二年級後的夏天開始服用 Ritalin。在他成長的 affluent neighborhood(富裕社區),SAT prep(SAT 準備)是一個重要的 rite of passage(成人禮),那個夏天,他的父母讓他報名參加當地 tutoring center(補習中心)的 prep course(準備課程)。Cap(a nickname)告訴我,他發現為 SAT 學習「very boring」(非常無聊),每次去補習時,他都感到 unable to concentrate(無法集中注意力)。
然後他被 prescribed(處方) Ritalin,他的 test prep(考試準備)經驗改變了。「I used to hate doing the SAT reading」(我以前討厭做 SAT 閱讀),Cap 說。「But if I took the medication, I could read through it all and, like, comprehend it really well. I would actually enjoy reading it.」(但如果我服用藥物,我可以讀完它全部,而且,像,理解得非常好。我會實際上享受閱讀它。)
Cap 是 varsity baseball team(校隊棒球隊)的成員,那年秋天有一天,他在 SAT tutoring sessions(SAT 補習課程)後直接去 batting practice(打擊練習)。令他驚訝的是,他發現藥物也幫助了他的 hitting(擊球)。「我非常 focused(專注),」他說。「My contact rate was higher.(我的接觸率更高。)I could see the ball better coming out of the machine.(我能更好地看到球從機器中出來。)」Cap 一直是一個非常 social(社交)的傢伙,baseball practice(棒球練習)通常是與隊友 chat and joke(聊天和開玩笑)的時間。但當他服用 Ritalin 時就不是了。「When I’m on the medication, I don’t get as distracted socially」(當我在藥物下時,我不會那麼容易在社交上分心),他告訴我。「It feels like you’re a horse with blinders on.(感覺就像你是戴著眼罩的馬。)You’re just focused on your goal.(你只是專注於你的目標。)There’s nothing else going on in your head.」(你腦中沒有其他事情發生。)
雖然他發現 Ritalin effective(有效)——無論對棒球還是 test prep(考試準備)——但他不喜歡它。「Honestly, I pretty much hated taking it」(老實說,我幾乎討厭服用它),他告訴我。「But I knew I needed to for my SAT.」(但我知道我需要為了我的 SAT。)他向我描述了藥物的 daily ups and downs(每日起伏),這不僅影響他的 mood(情緒)還影響他的 appetite(食慾)。「When I take it for studying, it does feel like I’m getting an adrenaline rush」(當我為了學習服用它時,確實感覺像得到一陣 adrenaline rush(腎上腺素激增)),他說。「I feel happy.(我感覺快樂。)When it peaks, you feel good about yourself.(當它達到高峰時,你感覺自己很好。)You’re studying, you’re locked in.(你在學習,你完全鎖定。)But then once it wears off, you just feel awful.」(但一旦它消退,你就感覺 awful(糟糕)。)
John,Cap 的 teammate(隊友),在八年級時第一次被 prescribed(處方) Adderall 來治療 A.D.H.D.。他告訴我,它幫助他度過他的 classes(課程),尤其是他從來不太喜歡的 English(英語)。「It would make it so that if I tried to pay attention, I would be able」(它會讓我如果試圖注意,就能做到),他告訴我。「It would still be very boring, but I was able to finish books and pay attention to what was happening.」(它仍然非常無聊,但我能夠完成書籍並注意發生的事情。)
不過,在社交上,有一個 price(代價)。「Around my friends, I’m usually the most social, but when I’m on it, it feels like my spark is kind of gone」(在朋友周圍,我通常是最社交的,但當我在它下時,感覺我的 spark(火花)有點消失了),John 說。「I laugh a lot less.(我笑得少多了。)I can’t think of anything to say.(我想不出任何話來說。)Life is just less fun.(生活只是少了很多樂趣。)It’s not like I’m sad; I’m just not as happy.(不是像我悲傷;我只是沒有那麼快樂。)It flattens things out.」(它把事情 flatten out(平淡化)。)
‘If I don’t have to do any work, then I’m just a completely regular person.’(如果我不需要做任何工作,那麼我就是一個完全 regular(正常)的普通人。)
當 John 和我交談時,已是夏末,他正準備前往大學 freshman year(大一)。我問他一旦到那裡,是否計劃服用 A.D.H.D. 藥物。他說是的,可能吧。他並不 crazy about the idea(瘋狂喜歡這個想法),但對他來說,這感覺像是一種 trade-off(權衡),最終會 worth it(值得)。「I kind of feel like it’s just a sacrifice I’m going to have to make」(我有點感覺這只是我必須做出的犧牲),他告訴我。
對其他青少年來說,stimulants(興奮劑)的 negatives(負面) outweigh the positives(勝過正面),他們 lobby(遊說)父母停止服用藥物——或者他們 just quit on their own(自己就戒掉)。統計上,大多數 adolescents(青少年)不會在 stimulants(興奮劑)上停留超過一年。對 Swanson 來說,高 quit rate(戒除率)是進一步證據,證明從 long term(長期)來看,這些藥物 just aren’t that good(就是沒那麼好)。「If it’s so effective, why do people stop?」(如果它那麼有效,為什麼人們會停止?)他問。「The physicians say, ‘They stop because they don’t know what’s good for them.’」(醫生們說,『他們停止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對他們好。』)所以父母聽到訊息:『If you don’t fill this prescription, you just don’t know what’s good for your kid.』(如果你不填這個處方,你就不知道什麼對你的孩子好。)But if you ask the kids themselves, they say, ‘It makes me feel bad.’ Or, ‘It didn’t help me.’ Or, ‘It stopped working.’ Who do you believe?」(但如果你問孩子們自己,他們說,『它讓我感覺不好。』或者,『它沒有幫助我。』或者,『它停止作用了。』你相信誰?)
A.D.H.D. establishment(體制)的一個 significant part(重要部分)確實 promote(推廣)這樣的訊息,即抵抗藥物的兒童和青少年 don’t know what’s good for them(不知道什麼對他們好)。當你閱讀 ADDitude 雜誌時,你經常遇到這種 point of view(觀點),該雜誌由線上出版商 WebMD 擁有。最近一篇故事的 headline(標題)寫道:「Half of College Kids Stop Taking Their A.D.H.D. Medication. Make Sure Your Teen Isn’t One of Them.」(一半的大學生停止服用他們的 A.D.H.D. 藥物。確保你的青少年不是其中之一。)另一篇文章,由 Wes Crenshaw 撰寫,建議父母「problematize」(問題化)他們孩子的 A.D.H.D. 以鼓勵他們服用藥物。「To accept treatment, teens need to feel A.D.H.D. as problematic, as a pain in their life that limits and controls them」(要接受治療,青少年需要感覺 A.D.H.D. 是 problematic(有問題的),是他們生活中 limits and controls them(限制並控制他們)的 pain(痛苦)),Crenshaw 寫道。「Too many parents normalize their children’s struggles to make them feel better.」(太多父母 normalize(正常化)他們孩子的 struggles(掙扎)來讓他們感覺更好。)
第三篇文章,由 Roberto Olivardia ——一位在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講課的 clinical psychologist(臨床心理學家)——撰寫,給臨床醫生建議如何回應,如果父母說他們擔心 stimulant medication(興奮劑藥物)正在 muting(消音/壓抑)他們孩子 sense of humor(幽默感)。建議的回應:也許你的孩子是 wrong kind of funny(錯誤類型的搞笑)。「Parents should know that not all personality changes sparked by medication are negative」(父母應該知道,不是所有由藥物 sparked(引發)的 personality changes(人格變化)都是 negative(負面的)),Olivardia 建議。「If a child known for his sense of humor seems ‘less funny’ on medication, it could be that the medication is properly inhibiting them. In other words, it’s not that the child is less funny; it’s that they’re more appropriately funny at the right times.」(如果一個以幽默感聞名的孩子在藥物下似乎『less funny』(較不搞笑),這可能是藥物 properly inhibiting them(適當抑制他們)。換句話說,不是孩子較不搞笑;只是他們在 right times(適當時間)更 appropriately funny(適當地搞笑)。)
Cap 的父母確實鼓勵他在高中期間每天服用他的 Ritalin,但事實上,他告訴我,他使用它 much more situationally(更情境化)。到 senior year(高三)結束時,他服用藥物參加 baseball games(棒球比賽)的次數比為了學習還多,而在週末和夏天,他 rarely took it(很少服用)。
John 通常在夏天也不服用他的 Adderall。當他不在學校時,他告訴我,他完全沒有任何 A.D.H.D. 症狀。「If I don’t have to do any work, then I’m just a completely regular person」(如果我不需要做任何工作,那麼我就是一個完全 regular(正常)的普通人),他說。「But once I have to focus on things, then I have to take it, or else I just won’t get any of my stuff done.」(但一旦我必須專注於事情,那麼我就必須服用它,否則我就不會完成任何我的東西。)
John 感覺他的 A.D.H.D. 是 situational(情境性的)——他在某些 circumstances(情況)下有,但在其他情況下沒有——這對精神醫學對這種狀況的一些 longstanding assumptions(長期假設)構成挑戰。畢竟,diabetes(糖尿病)不會在 summer vacation(暑假)中消失。但 John 的 intuition(直覺)得到科學證據的支持。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對許多人來說,A.D.H.D. 可能被視為他們 experience(體驗)的 condition(狀況),有時是 temporarily(暫時的),而不是他們以某種 unchanging way(不變方式)擁有的 disorder(障礙)。
去年十月,M.T.A. 組發表了一項新研究,探討 M.T.A. 參與者的 A.D.H.D. 症狀在他們 childhood(兒童期)和 young adulthood(年輕成人期)過程中如何變化。與 A.D.H.D. 的 categorical model(分類模型)——你 either have it or you don’t(要麼有要麼沒有)——相反,研究人員顯示,對大多數受試者來說,他們的症狀和 impairment(損害)水平事實上在多年中 fluctuated(波動),往往 quite substantially(相當大幅)。只有約 11% 進入研究時有 A.D.H.D. 診斷的兒童年復一年 consistently(持續)體驗症狀。更常見的是,他們的症狀 would come and go(來來去去);幾年內,它們可能 stay above the D.S.M.’s symptom threshold(停留在 D.S.M. 的症狀閾值之上),然後幾年內,他們的 symptom count(症狀計數)可能 dip below the cutoff(降到截止點以下),有時 disappearing altogether(完全消失)。
「Rather than trying to treat and resolve the biology, we should be focusing on building environments that improve outcomes and mental health.」(而不是試圖治療和解決生物學,我們應該專注於建立改善 outcomes(結果)和 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的環境。)
當我和 Margaret Sibley —— fluctuation study(波動研究)的 lead author(主要作者),以及華盛頓大學醫學院(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Medicine)的 clinical psychologist(臨床心理學家)和 professor(教授)——交談時,她為我指出了一項來自較早 M.T.A. 論文的 curious finding(好奇發現):不僅大多數 A.D.H.D. 受試者至少 temporarily(暫時)改善,而且 comparison group(對照組)中的 40% 兒童——他們最初被選入研究正是因為他們沒有 A.D.H.D.——在 adolescence(青春期)的某個點有足夠的症狀來 qualify for an A.D.H.D. diagnosis(符合 A.D.H.D. 診斷)。
西布利(Sibley)告訴我,她不相信那些孩子在青少年時期突然罹患A.D.H.D.。相反,她說,他們的處境——他們的環境——可能已經改變,而這種環境的轉變可能加劇了他們的症狀。西布利說,重要的是要記住,A.D.H.D.的許多症狀其實相當常見;她解釋,在任何給定的時刻,平均美國成人都有兩三個這樣的症狀——距離正式診斷只有一半。「這不是你完全沒有或全部都有的東西,」她說。「這就是為什麼這是一種灰色疾患(gray disorder),當它不在極端時。」
然而,那些極端情況非常重要。將A.D.H.D.視為是或否、非黑即白的診斷,就像這個專業經常做的那樣,掩蓋了某些有A.D.H.D.症狀的孩子比其他人面臨更大風險的事實。奧勒岡衛生與科學大學(Oregon Health & Science University)的臨床心理學家喬爾·尼格(Joel Nigg)已經在A.D.H.D.人群中識別出多種不同的亞型(subtypes)。其中一組孩子,那些A.D.H.D.症狀伴隨著強烈憤怒的孩子,比僅有A.D.H.D.症狀的孩子面臨負面結果的風險高得多。他們的早期症狀,尼格發現,往往是診斷級聯(diagnostic cascade)的開始,導致青少年和成年期的真正問題,包括輟學、犯罪行為以及嚴重傷害或早逝的風險升高。那些患者,佔診斷為A.D.H.D.兒童的約三分之一,需要早期關注和全面治療——很可能包括藥物,但往往遠不止於此。
尼格懷疑那些高風險孩子確實與典型孩子有顯著的生物差異,他認為隨著這些技術的不斷改進,那些差異最終可能在基因測試或腦部掃描中出現。但對於診斷為A.D.H.D.的相當比例的人來說,尼格說,「他們在神經生物學上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相反,他們的症狀是情境性的(situational)或條件的(conditional)。他們可能經歷了艱難的生活,或者缺乏社會支持,或者他們處於生活中的錯誤利基(wrong niche)。」
如果他們的問題根源於環境如同腦化學一樣,尼格相信,那麼或許他們的治療也可以基於環境。索努加-巴克(Sonuga-Barke)同意。在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他擁抱他現在稱為A.D.H.D.的「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相信A.D.H.D.患者的腦部在生物上缺陷,與典型、健康個體的腦部有類別上的不同。然而現在,索努加-巴克提出一個替代模式,一個很大程度上迴避生物學問題的模式。他說,重要的是孩子在試圖在世界上闖蕩時感受到的困擾(distress)。
索努加-巴克提出的模式將A.D.H.D.症狀定位在一個連續體(continuum)上,而不是將這種狀況呈現為一個獨立的、自然類別。而且它在另一個關鍵方式上偏離醫療模式:它將那些症狀視為孩子生物組成(biological makeup)與他們試圖運作的環境之間不對齊(misalignment)的信號,而不是神經缺陷(neurological deficits)的指示。「我不是說它不是生物的,」他說。「我只是說我不認為那是正確的目標。與其試圖治療和解決生物問題,我們應該專注於構建改善結果和心理健康的環境。」
改變一個人的環境真的能改變他們的症狀嗎?在2016年,艾麗爾·拉斯基(Arielle Lasky)和M.T.A. 研究小組(M.T.A. research group)的成員發表了一篇論文,建議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答案是肯定的。在研究歷史的那個時間點,受試者是20多歲的成年人,能夠為自己發聲。因此,科學家不僅僅收集他們症狀或身高的數據,而是問他們問題。他們對125名這些年輕成年人進行了長時間訪談,所有這些人都在兒童時期被診斷為A.D.H.D.。
研究人員注意到的是,他們的受試者並不特別感興趣談論他們疾患的具體細節。相反,他們想談論他們現在生活的脈絡(context),以及那個脈絡如何影響他們的症狀。一個接一個的受試者自發地提起找到他們的「利基」(niche),或在學校或職場中的正確「適合」(fit)的重要性。作為成年人,他們比兒童時期有更多自由來控制他們生活的參數——是否上大學、學什麼、追求什麼樣的職業。他們中的許多人明智地選擇了比他們在學校經歷的更適合他們個性的脈絡,結果,他們報告他們的A.D.H.D.症狀基本上消失了。事實上,他們中的一些人正在質疑他們是否曾經有過疾患——或者他們只是兒童時期處於錯誤的環境中。
「將A.D.H.D.描述為一種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而不是疾患,他們視自己為不同而不是缺陷的(defective)。」
受試者茁壯成長的工作環境各不相同。對一些人來說,他們新工作的吸引力是忙碌且認知需求高,需要持續的多任務處理(multitasking)。對其他人來說,正確的脈絡是身體的、動手的勞動(hands-on labor)。對他們所有人來說,產生差異的是擁有對他們來說感覺「內在有趣的」(intrinsically interesting)工作。
一位在大學學習電影的受試者說,他在所選領域茁壯成長的能力讓他質疑他花費治療A.D.H.D.的那些年。「最初,當我第一次被診斷時,它被解釋為注意缺陷(attention deficit),只是缺乏注意,」他說。「一種無法長時間擁有注意持續時間(attention span)的能力。但對於我關心的事物,我可以擁有極長的注意持續時間。」這位電影學生反思了他早期的掙扎。「公立教育(public education),你是被迫進入的,」他說。「也許那就是為什麼我沒有那麼注意。但現在我在大學,在一個我想參與的主題中,所以我缺乏注意的情況幾乎不再發生,因為我通常不會在我不想要的地方。」
一位髮型師(hairstylist)告訴研究人員,她在學校無法集中注意力的情況,在她開始學習美髮時消失了。「如果你坐在那裡給我講授關於髮的課程,我會逐字逐句記住你說的話,」她說。「我感興趣的事物,我會完全沉浸其中。但在學校裡,那真是糟糕。」
一位正在培訓成為汽車技師的年輕男子說,在他的新職業中,他的 A.D.H.D. 不再是問題。「只是我需要弄清楚我想做什麼,」他解釋。「我想從事汽車相關的工作。我做那件事不會感到無聊。」如果有 A.D.H.D. 的人被引導到他們優勢和興趣所在的領域,他繼續說,「我相當確定他們可以自然地應對它,而不是不得不給人們服用藥物。」
瑪格麗特·西布利(Margaret Sibley)最近的波動性論文(fluctuations paper)提供了一些額外的線索,關於什麼可能幫助青少年和年輕成人感覺更好並更好地運作。讓西布利驚訝的是,患者的症狀傾向於在「環境需求更高」(environmental demands)的時期改善,而不是惡化——這些時期有更多責任和更繁忙的時間表。對於「niche」研究中的許多許多年輕男性和女性,同樣的現象成立:要求高且有趣的工作或大學課程有助於緩解他們的症狀。當他們的症狀緩解時,他們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
「而不是在所有情況下出現的靜態『注意缺陷』(attention deficit),」M.T.A.研究人員寫道,「我們的受試者描述他們的注意力分散的傾向是脈絡性的(contextual)。……相信問題在於他們的環境而不是僅僅在他們自身,這有助於個人減輕不足感:將 A.D.H.D. 描述為一種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而不是疾患,他們視自己為不同而不是缺陷的(defective)。」
透過這個視角(lens),約翰(John)、卡普(Cap)和其他許多青少年的問題變得比腦部疾患(brain disorder)更平凡得多。他們的問題只是高中可能真的很無聊這個簡單事實,而且沒有藥物,他們對無聊事物有低耐受性(low tolerance)。對某些孩子來說,一所不同的學校,或不同類型的學校,可能會產生與M.T.A.受試者在註冊電影學校或開始學習美髮造型時經歷的同樣深刻轉變。對其他人來說,利他能(Ritalin)或愛得樂(Adderall)的處方可能有助於讓學校感覺更適合。但對他們和他們的父母來說,服用藥物的經驗可能會感覺相當不同,如果它被呈現為不是修復他們缺陷腦部的藥物,而是讓不友善環境(inhospitable environment)更可忍受的工具。
當埃德蒙·索努加-巴克(Edmund Sonuga-Barke)思考注意力問題如何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演變和改變時,他經常想到自己的故事。在1960年代的德比(Derby)長大,一個英國中部(Midlands)蕭條的工業城市,他在課堂上無法坐定。在8歲時,他被評估為過動症(hyperkinesis)和最小腦功能障礙(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那是當時用來稱呼我們現在稱為A.D.H.D.的術語。他沒有接受任何治療或藥物;相反,他被降到補救班(remedial class)。他從學校的羞恥和無聊中找到的唯一解脫是與他的朋友們,一群粗魯且準備好的年輕叛逆者,他們在青少年時期因對龐克搖滾(punk rock)的熱愛而結合。
然後,透過一系列奇蹟般的干預,索努加-巴克獲得了獎學金去上大學——威爾斯(Wales)的班戈大學(Bangor University)。當他搬到威爾斯鄉村時,他突然發現自己處於一個與他成長所知的一切都非常不同的環境中。
對於「niche」研究中被訪談關於工作生活的年輕成年人來說,幫助他們克服A.D.H.D.症狀的轉變往往是離開學術工作轉向更動感的(kinetic)事物。對索努加-巴克來說,則是相反。在大學,他每天早上9點出現在圖書館,坐在他的小隔間(carrel)工作直到5點。第二天,他會再做一次。他說,在成長過程中,他有自然傾向於「過度專注」(hyperfocus),而在德比的學校,那種傾向在他的老師看來像是白日夢(daydreaming)。在大學,它成為他的秘密武器(secret weapon)。
「我認為我的大腦可能已經成熟到我先前沒有能力的程度,」索努加-巴克告訴我。「同時,突然我處於一個我的自然思考方式有價值的脈絡中。這兩者的結合對我來說是啟示性的(revelatory)。」他從班戈畢業,獲得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然後繼續獲得學術聲望的職位,包括當選醫學科學院(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院士,並被任命為《兒童心理學與精神病學期刊》(The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的總編輯(editor in chief)。
我問索努加-巴克(Sonuga-Barke),如果他成長在不同的時代和地方——如果他在8歲時被開立利他能(Ritalin)或愛得樂(Adderall),而不是只是被打包送到補救班(remedial class)——他可能會獲得什麼。
「我不認為我會獲得任何東西,」他說。「我認為沒有藥物,你會學會應對事物的替代方式。在我的特定情況下,有很多特徵幫助了我。我的腦袋不斷運轉,思考事物。我從不放鬆。我激勵自己的方式是將一切轉化為問題,並試圖解決問題。」
索努加-巴克說,他認識許多年輕人,包括他自己家庭中的一些人,從服用興奮劑藥物(stimulant medication)中受益。他只是不認為將愛得樂(Adderall)或利他能(Ritalin)視為醫療疾患的醫療解決方案是準確的——或有幫助的。
「簡單的模式基本上一直是『A.D.H.D. 加藥物等於沒有A.D.H.D.』,」他說。「但那不是真的。藥物不是萬靈丹(silver bullet)。它永遠不會是。」他相信,藥物有時能做的是讓家庭有更多溝通空間。「在其最佳情況下,」他說,「藥物可以為父母提供一個與孩子互動的窗口,」透過至少暫時緩和孩子的行為,讓家庭生活不僅僅是關於逾期作業和丟失午餐盒的無盡爭吵。「如果你與孩子有更正面的關係,他們會有更好的結果。不是為了他們的A.D.H.D.——它可能還是會一樣。但在處理往往伴隨著A.D.H.D.的自恨(self-hatred)和低自尊(low self-esteem)方面。」
「診斷可能創造一個增強偏見(prejudice)和判斷(judgment)的身份,這些與更大的孤立(isolation)、排除(exclusion)和羞恥(shame)感覺相關。」
那可能聽起來有點模糊(mushy)——A.D.H.D.治療的目的是幫助你建立關係並改善你的自尊,而不是更科學聽起來像是修復你故障腦部(malfunctioning brain)的目標。但回想馬蒂娜·霍格曼(Martine Hoogman)2017年論文中那個有爭議的陳述。她寫道,重要的是將Enigma數據解釋為確認A.D.H.D.患者「有改變的腦部」(altered brains),因為那種生物解釋將「有助於減少A.D.H.D.的汙名」(stigma)。但將A.D.H.D.描繪為「腦部疾患」(disorder of the brain)真的會減少它的汙名嗎?事實上,它難道不會增加年輕人的羞恥感和孤立感,被告知他們有腦部疾患?
一位名叫路易絲·卡茲達(Luise Kazda)的澳洲心理學家已經研究了這個問題。在2021年的一篇回顧論文中,她和她的同事發現14項研究,其中接受A.D.H.D.診斷創造了一種「賦權」(empowerment)的感覺,透過「支持合法感,伴隨著理解和同情,以及減少內疚、責備和憤怒」。但在另外22項研究中,卡茲達寫道,「生物醫學觀點(biomedical view)的困難被證明與去賦權(disempowerment)相關。透過為問題提供藉口,所有相關人士的責任減少,可能接著是無行動和停滯(inaction and stagnation)」。另外14項研究發現,診斷增加了汙名化的感覺。「診斷可能創造一個增強偏見(prejudice)和判斷(judgment)的身份,」卡茲達報告,「這些與更大的孤立(isolation)、排除(exclusion)和羞恥(shame)感覺相關。」
目前仍不完全清楚,為什麼簡單地提供A.D.H.D.診斷的行為似乎對某些孩子和他們的家庭有如此深刻的影響。但在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下,診斷傳遞的訊息確實與像索努加-巴克(Sonuga-Barke)的模式非常不同,後者將一個人的A.D.H.D.症狀視為,至少部分是,與特定環境不匹配(mismatch)的產物。
對某些父母來說,確實可能較少汙名化,也更舒適,能夠說:「我的孩子有A.D.H.D.,一種醫療狀況,所以他需要每天服用這種藥物」,而不是:「我想讓我的孩子在不適合他的環境中成功,因此我想讓他服用這些藥丸。」然而,對許多孩子來說,透過主流醫療模式傳達的A.D.H.D.診斷可能感覺不僅僅是汙名;它可能感覺像終身監禁(life sentence)。傳遞給孩子的訊息往往是A.D.H.D.是一種二元(binary)、生物類別(biological category),如果你的症狀將你置於那個類別,你的腦部有缺陷(deficit),你有疾患。
相反,替代模式告訴孩子一個非常不同的故事:他的A.D.H.D.症狀存在於一個連續體(continuum)上,我們所有人都處於其中;他可能正經歷那些症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身處何處,而不是因為他是誰;明年,如果他的周圍環境改變,那些症狀也可能改變。配備這種理解,他和他的家人可以決定藥物是否合理——對他來說,好處是否可能大於缺點。同時,他們可以考慮在學校或家中的情況是否有變化,可能有助於緩解他的症狀。如果他也經歷其他心理狀況——焦慮(anxiety)或憂鬱(depression)或創傷後壓力(post-traumatic stress)——他們可以採取步驟來處理那些更深層的問題,獨立於他在數學課無法專注的能力。
誠然,那種版本的A.D.H.D.有某些缺點。它否認父母對孩子問題的清晰、明確解釋,那種解釋可能帶來如此大的解脫,尤其是經過數月或數年的挫折和不確定之後。它往往需要患者、家庭和醫生方面的許多彈性(flexibility)和實驗(experimentation)。但它也有兩個重要的優勢:首先,新模式更準確地反映了A.D.H.D.的最新科學理解。而且其次,它給孩子一個他們未來可能真正改善的願景——不是因為他們的腦部被化學重塑(chemically refashioned)以使他們更好地適應世界,而是因為他們找到一種讓世界更好地適應他們複雜且獨特的腦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