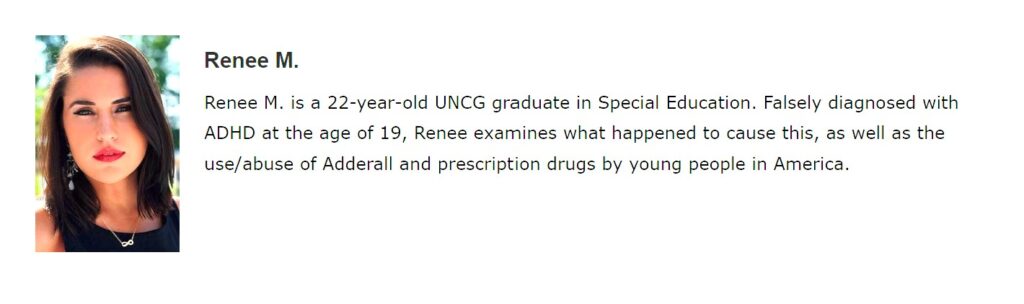我的多動症(ADHD)診斷及隨之而來的低谷
作者:Renee M. – 2016年1月26日
隨著我邁向社會工作碩士學位的過渡期,我決定分享我使用精神科藥物處理診斷的經歷。從診斷到我進入12步驟康復計劃的時間並不長,但在這段時間內發生了很多事情。回頭看,事情總是清楚的,因此我希望能回顧幾年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給與此領域或有類似診斷的人提供一些見解。
我在19歲時被誤診為ADHD(注意力缺陷多動症),我想檢視導致這一誤診的原因。這其中有很多原因,而在診斷後被處方了Adderall(阿得拉)後,對我造成了許多不良影響。這個故事講述了導致我一生中最不利診斷的原因。
ADHD,即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現在是一個常見的術語。每天在廣告、玩笑、學校和心理健康場所中都會提到它。這個詞彙在流行文化中的頻繁出現,幾乎使其正常化。經常與被診斷為ADHD的人相處,聽到名人被診斷出來,並參與使用這個縮寫的玩笑,這一切都讓我對這個診斷變得麻木。這種社會上對ADHD的接受態度最終讓我認為被診斷為ADHD也沒有什麼不妥。
在小學的每一年,我都要參加專注力測試和問題測驗,我總是希望自己能通過並獲得診斷。在家裡,我曾向父母建議我可能有ADHD。他們會回應:“每個人都多多少少有些ADHD,你不需要吃藥!” 從父母的反應中,我反叛了這種“不需要藥物”的觀念。我覺得那些被處方了這種“專注力藥物”的學生有優勢,而我沒有這樣的解決方案。
我在初中和高中的最好朋友被診斷為ADHD。她的母親剛好是精神科醫生,所以她“有門路”,我當時這樣認為。她還被診斷了其他幾個標籤,並得到了相應的處方藥。在午餐時,我們經常討論她因為藥物無法吃東西。這讓我很興奮,因為她會把食物給我。我和我的朋友討論過幾次Adderall,有一次她特別告訴我:“沒有這些藥,我什麼都做不了!它們幫助我起床。” 當時我不太理解她為什麼需要這些“專注力藥片”來起床,我以為她是為了學校需要它們,而不是為了起床而需要能量。
隨著時間的推移,服用刺激藥物的人會迅速減重這一點也變得讓人向往。我認識一些朋友,專門購買這些刺激藥物來減肥。它們迅速成為懶女孩的奇跡減肥藥!在我天真的心中,我認為這種藥物可以解決我的所有問題。
我第一次嘗試Adderall是在我參加SAT(美國高考)時。我看過一些熱門電影和電視節目,這些藥片幫助沒有準備的學生奇跡般地應付考試。一位被處方藥物的朋友聽到我說我沒有學習,她便給了我幾片Adderall來“解決”我的問題。我欣然接受,根本沒想到後果。在SAT考試期間,我異常興奮。我記得在休息時間,我會告訴同學我有多麼期待再次進入考場繼續考試。他們都看著我,好像我在吸毒(事實上我確實是這樣的)。
高中時,由於我的優先事項混亂,我的課業表現並不突出。到了大學,我的優先事項徹底改變,我終於理解了學校的價值。在大學一年級,我的生活包括上課、學習和派對。我進入了校長名單,但仍然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時間從事課外活動。我在大一期間只吃過一兩次Adderall。
儘管在沒有處方Adderall的情況下,我在大學表現出色,但我還是說服自己需要它。我說服媽媽讓我去見一位長老會的諮詢師,以確定我是否真的有ADHD。我事先研究了應該說什麼以便得到診斷,於是我做好了準備。這次沒有任何談話治療,只有一份簡單的問題清單,然後結果是:“你有ADD,不是多動型,但仍屬於ADHD範疇。我們先讓你開始使用一種非刺激性處方藥。”
這次簡單的初次拜訪陌生的諮詢師結果是我的ADHD診斷。這次拜訪也開啟了我藥物濫用的雪崩。我19歲時被誤診為ADHD,這永遠改變了我的生活。
診斷後,我立即被處方了非刺激藥物Strattera(思瑞康)。知道之前Adderall帶給我的感覺,我決心獲得這種藥物。大約在服用Strattera的第二周,當劑量從約15毫克增加到40毫克的那一天,我出了車禍。我停在紅燈處,感覺精神恍惚,卻又異常專注。我唯一記得的是,我低下頭但從餘光中看到燈變了,於是我踩了油門。前面的人走得慢了點,我直接撞上去,撞毀了我的車。意識到自己剛做了什麼後,我幾乎崩潰,哭得非常厲害——而我平時並不是會哭的人。
這場可怕的“車禍”幾乎立即預示了我在隨後幾年中因精神科藥物而遭遇的災難。對Strattera造成的影響充滿怨恨,我更加決心以這件事為借口說服精神科醫生讓我試試刺激藥物Adderall。幾乎毫不費力,尤其是在我有了ADHD的正式診斷後,我真的認為自己需要這種藥物來取得生活的成功。我與同齡人討論過應該告訴醫生哪些症狀,以便讓她提高我的劑量。在我看來,19歲時不僅被首次診斷為ADHD,而且在幾周內就獲得了25毫克XR的Adderall一個月的供應量,這實在是太容易了。
像我這個年齡和體重的人不應該被處方這麼多或這麼高的劑量。我的身體不知道如何應對它。我減掉了20到30磅,而我本來已經夠瘦了。隨著我現在擁有的大量供應,加上周圍大學生的需求,我開始販賣這些藥片。每天吃一片25毫克的XR足以讓我感到精力充沛。我感覺過於興奮,如果不想整天顫抖,我會把膠囊拆開,只吃一半。
我的精神科醫生最初只想每個月見我一次,確保藥物“有效”。她曾決定對我進行一次藥物測試,以確保我按照處方服用。由於我正按照她給的極端劑量服用,加上其他藥物,測試結果沒有問題,什麼也沒說。
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我意識到自己如果不吃這片藥就無法起床。它成為了我的好朋友、收入來源和新的能量來源。大約六到八個月後,我開始經歷極大的焦慮和抑鬱。而且我幾乎無法入睡。為了對抗Adderall給我身體和心理帶來的副作用,我開始大量吸食大麻。我還會偶爾服用朋友給的處方藥如Xanax(抗焦慮藥)或止痛藥。這些藥物有助於緩解Adderall對我身體和精神的日益增加的副作用。
慢慢地,我開始注意到自己性格的變化。我開始利用人來獲取藥物,這些藥物可以對抗我以為自己需要的藥物的副作用;畢竟,醫生診斷我了!Adderall讓我變得易怒和暴躁。在我曾經能輕鬆應對的社交場合中,我開始分析自己做的每一個動作和說的每一句話。
情況變得如此糟糕,我不得不將鬧鐘設早30分鐘,然後吃一片Adderall,躺在床上等待它生效。如果我用完了藥,不得不忍受周末的等待,那我幾乎不會動一根手指。我有過一些清醒的時刻,我覺得如果我停止服用這種“上癮藥”(Adderall),我可能就不需要這麼多“鎮靜藥”(酒精、毒品)了。但這個想法很快被我那“我需要它來學習”的思維掃地出門,忘記了自己在大一時沒有服用Adderall時也學得很好。我是在大一的夏天被處方的——情況逐漸惡化,直到大三末期我墮落到如此低的谷底,這才迫使我戒掉毒品。
戒毒的過程包括徹底撕掉創可貼。我沒和精神科醫生談過這件事,因為我從來不和她談任何事。戒斷後我有時會頭痛。重新依賴自己來應對日常生活的過渡期非常艱難。
我的Adderall經歷在短短幾年內開始和結束,但它幾乎掌控了我的生活。精神科醫生沒有警告我危險,也沒有真正關心它如何影響我。我本質上是被診斷、處方了藥物,然後被丟在一邊,直到它幾乎摧毀了我。我強烈建議大家在信任心理健康診斷和服用精神科藥物以真正改善或治癒自己時,保持謹慎和警覺。
自從停藥後,我的情感回來了。我並不總是感覺很好,但至少我現在有了感覺。我不再需要設兩個鬧鐘,靠一片藥來把我叫醒。不必依賴藥片來完成日常功能,這感覺棒極了。我現在可以真正享受食物的味道——多麼大的啟示啊!我已經健康地增重了10磅,現在125磅,對自己的身體形象感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樂。當我服用Adderall及其他藥物來保持平衡時,我的靈性幾乎不存在,或者到了最後,完全扭曲了。現在我可以對自己的決定感到滿意,並依賴我的更高力量/更高自我,而不是讓精神科藥物成為我的更高力量。
當我用處方藥和非處方藥掩蓋所有問題時,我並沒有真正生活,而現在我有機會做出真正的選擇,我能夠感覺到這些選擇對我來說是正確的。我可以聽從身體的需求,而不是迫使身體聽從我的自我慾望。我變得更堅強,學會如何再次處理我的情緒,而不是迫使它們不存在。冥想對於我的“專注問題”幫助極大——我現在感覺它們根本不影響我的生活。我現在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沒有那些我以為是拐杖的東西拖累著我。
【編者註:作者選擇以縮寫名發表此文,因其正在申請研究生學校的過程中。】
Renee M.
Renee M. 是一位22歲的UNCG特殊教育畢業生。她在19歲時被誤診為ADHD,並檢視了導致這一誤診的原因,以及美國年輕人使用/濫用Adderall及處方藥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