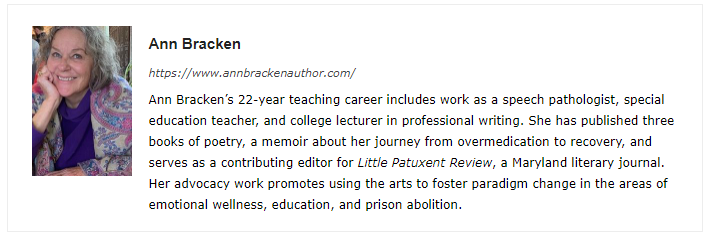育兒改變了我對「ADHD」的看法
作者:安·布拉肯,2022年3月18日
當我在1974年大學畢業時,我認為自己已經為在公立學校擔任語言病理學家做好了充分準備。我知道如何使用發音測試來篩查語言延遲和發音問題。通過各種標準化和非正式的評估,以及教師的意見,我可以確定孩子在語言理解和表達方面的困難。我能夠輕鬆地進行例行的聽力篩查,以確定孩子是否需要完整的聽力學檢查。然而,對於那些被標籤為「過度活躍」的孩子,我卻沒有做好向家長提出建議的準備。
在我進入學校工作的第二年,我的一項職責是參與篩查委員會。學校的篩查委員會由副校長、學校心理學家、閱讀專家、推薦的班級教師以及語言病理學家(我)組成。孩子們因各種問題被推薦至委員會,例如閱讀或數學困難、語言或聽力問題,以及後來被重新命名為注意力缺陷多動症(ADHD)的「過度活躍」。
在篩查委員會的討論中,有三個關於這些被老師或家長認為是過度活躍的孩子(幾乎總是男孩)的特點讓我印象深刻。當我們調查孩子的資料時,幾乎總是發現他們有一個我們委婉稱為「晚生的生日」,因為他們的生日接近年底。這意味著他們通常是班上年紀最小的孩子。此外,當我們調查孩子的家庭狀況時,往往發現父母最近剛剛離婚,或者家庭中有人過世。最後,委員會中總有人(通常是副校長或學校心理學家)建議家長為孩子尋求藥物諮詢。
當時,利他林(Ritalin)似乎是最常用的藥物,並且家長通常會配合。在兩到三個月內,當委員會跟進孩子的進展時,老師通常會報告孩子有了改善,因為他能坐在座位上,遵守指令,並完成作業。關於藥物的抱怨通常來自家長,因為孩子會有睡眠困難或食慾不振的問題。我還記得聽到過類似的話:「當藥效消退時,他似乎變得非常煩躁。」或者「週末他總是精力過剩。」
當我向學校心理學家詢問類似利他林這種興奮劑的效果時,他只告訴我,這種藥物在有過度活躍的孩子身上會有不同的作用,幫助他們在學校集中注意力。而只要家長在週末和暑假期間讓孩子暫停用藥,食慾、成長和睡眠的問題應該會正常恢復。由於我在大學時的特殊教育入門課程幾乎沒有涉及藥物方面的內容,我以為這些就是我需要知道的全部了。
我的兒子被貼上標籤
在我的孩子出生後,我於1980年代停止了語言病理學家和特殊教育教師的工作。他們兩個似乎都按時達到所有的發展里程碑,並在上幼稚園前開始識字。他們喜歡用藝術材料創作、在森林裡建造堡壘和騎自行車。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我會被叫去參加會議討論學習或行為問題。
康納很快適應了幼稚園的日常,但他告訴我,有時候他不想做分配的課堂活動,所以老師就讓他在課間時間待在教室裡。儘管如此,他整體表現很好,並且充滿熱情地開始了第一年級。他有很多朋友,能輕鬆完成所有的功課,似乎真的很享受上學。因此,當老師告訴我她對他的進步不滿意時,我感到非常震驚。當我來到會議時,她帶我走到他的桌子旁,那裡堆滿了未完成的作業紙。
「我認為你應該帶康納去檢查一下是否有注意力缺陷多動症(ADHD),」她告訴我。
「什麼?康納可以自己玩樂高幾個小時,他第一次聽到我叫他做事時就會照做,而且我在家裡沒有遇到任何嚴重的紀律問題。我不明白。」
「他有一大堆未完成的作業,而這通常是這種障礙的跡象。」
我和丈夫都對老師所說的話感到震驚。那年夏天結束時,我們就要搬家了,這意味著康納會在新學校重新開始,所以我們決定靜觀其變,看看新老師會有什麼建議。
如我們所料,康納輕鬆地適應了新學校,交了幾個朋友,看起來在課堂上表現得也不錯。但有一天,他和一位朋友在課堂上玩鬧,康納伸出腳絆倒了那個男孩。他的老師要求我到學校參加會議。康納在辦公室裡等著我,當他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後,他說:「媽媽,我已經向馬克道歉了,我不是故意傷害他的。」根據老師所說,馬克看起來沒事,但她希望這些惡作劇停止。我向她保證,康納不會再有任何問題。當我離開學校時,校長抓住我,嚴厲地要求:「控制好你的孩子。要麼你給那個男孩吃藥,要麼我會處理。」
我從未想過康納需要任何藥物來控制他的行為。他基本上是一個可愛的孩子,但就像所有孩子一樣,有時也會有些衝動。他真的需要藥物來控制這些嗎?我跟他的兒科醫生談了,醫生給了我兩份檢查表——一份給我,一份給他的老師。老師的擔憂比我多,所以醫生建議讓康納開始服用利他林來幫助他控制衝動。我信任這位醫生,所以我們告訴康納他會服藥,以便能在學校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幾天後,我在晚上哄他睡覺時,他問我:「媽媽,這顆藥會讓我變好嗎?」
他的問題讓我感到不安,於是我決定找一位兒童心理學家來提供更多指導。心理學家對診斷症狀的調查表不以為然,說:「在開始給孩子服用利他林之前,肯定需要的不只是兩個人的意見。」接下來的兩個月裡,他多次與康納見面,也和我及我丈夫進行了交談,並對康納的學業成績進行了評估。他的結論是:「除了在學校有點無聊,康納是一個行為良好、正常的孩子。我建議當他完成常規作業後,可以給他一些額外的活動。而且你可以停止給他服用利他林。」
然而,康納在學校的困難依然存在。回想那些年,我現在明白了,因為他在學校裡沒有受到挑戰,所以他覺得完成某些作業沒有意義。他只學習了為了通過考試所需的知識,其他的就忽略了。他沒有以特別優異的成績從高中畢業,然後過了幾年才開始上大學。當他拿到第一學期的成績時,他所有的課程都得了A。
「康納,你的成績很棒。和高中時的成績相比,現在有什麼不同呢?」
「很簡單,媽媽。大學的成績是有用的。」這個道理讓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完全理解。康納告訴我,他關心大學的學業,因為他選修了他感興趣的課程,而且他知道如果表現得好,這些成績可能會給他帶來實習或工作的機會。
我重返教室
在休息了20年後,我於2000年重新開始擔任特殊教育教師。由於我的資格非常搶手,找工作並不困難。我在幾所高中任教,包括公立和私立學校,還有一家精神病院的高中課程。這些學校看起來和我1980年代離開時差不多——教室前面擺放著老師的桌子,一兩個黑板,學生的桌子整齊地排成一排。有些老師甚至在地板上貼了膠帶來標示桌子的位置。
憑藉我在英語和閱讀方面的雙重資格,我經常與英語教師配對,採用所謂的共同教學模式。通常,這意味著我要幫助那些有個別教育計劃(IEP)的特殊教育學生。我幫助他們撰寫論文,整理筆記,並完成指定的項目。
然而,儘管教室的佈局和許多教學方法多年來幾乎沒有變化,但我已經變了。特別是在我看待那些被標籤為有ADHD的學生時(通常還是男生)。由於我有過康納因無聊而行為不端或未完成作業的經歷,我現在以更寬容、少些評判的眼光看待我的學生。康納幫助我意識到,我曾經試圖讓他適應傳統的學校成就模式;幸運的是,他的成功讓我學會了珍視其他的學習途徑。
我不再把那些想打擾課堂的孩子視為問題學生,而是看作因無聊或感到力不從心的孩子。像是在桌上來回滾動鉛筆,然後掉下來,再把椅子往後傾去撿鉛筆的行為,對我來說是學生要麼需要其他活動,要麼是因為尷尬而不敢尋求幫助。而那些不停在課堂上搶答或在上課中間開大聲玩笑的學生,通常是因為對某些課堂內容感到困惑而感到沮喪。當有學生在椅子上不停搖晃,或頻繁走到垃圾桶或削鉛筆機的時候,通常意味著他需要消耗一些精力——所以我會邀請他們和我一起繞著學校走幾圈。我們有機會談論課堂內容,也進行了一些運動。雖然孩子們經常在我說「我們出去走走」時嘟囔抱怨,但我們最終通常都會有一次愉快的交談。由於有了一對一的時間,學生感覺自己變得特別,而不是因為無聊或困惑而失去興趣。
隨著我更了解這些學生,我發現一些難以集中注意力或完成作業的學生也在家裡面臨著困難。一個男孩與他的叔叔和嬸嬸同住,因為他的父母酗酒,無法照顧他。他是一個聰明且有創意的人,喜歡寫作和打鼓。另一個男孩的家庭曾經無家可歸,直到他們搬到叔叔家。有一天,他告訴我,他們一家四口現在和叔叔一家七口共住在一間三居室的聯排別墅裡。難怪他下午總是趴在桌子上,並且在閱讀技能上落後。這兩個年輕人都有很多分心和無法專注的理由。
作為父母,我學到的最大教訓之一就是教孩子一些自我管理的技巧——當他們感到沮喪或憤怒時該做什麼,如何管理焦慮情緒,以及如何將一個大的任務分解成更小的部分。由於我們家裡總有黏土,我建議孩子們當感到生氣時,可以捏打黏土來發洩。我的女兒在考試前經常非常緊張,所以我教她如何安靜地坐著,深呼吸,並給自己重複一些積極的話。而當孩子們有長期的項目,比如閱讀一本書並製作海報展示時,我會幫助他們列出需要做的事情,然後在他們的作業計劃中安排不同任務的時間。
這些育兒工具以及我撫養一個聰明且有創造力但不符合常規的兒子的經歷,幫助我以更具同情心和創造力的方式對待我的學生。即便是像湯米這樣的一個九年級男孩(假名),他考驗了我所有的耐心。湯米服用了某種興奮劑,但到了放學時,他似乎已經筋疲力盡。他經常大聲打岔,開玩笑,並隨意走到教室後面削鉛筆——這些行為都讓他避免了當天的課堂作業。
我被分配為他的個案管理員,這意味著我要與湯米的所有老師協調幫助他的工作,跟蹤他的進度,並定期與他媽媽(假名米勒太太)溝通。有一天,米勒太太打電話給我,顯然已經失去耐心。她滔滔不絕地列舉了湯米在家裡和學校的所有問題,最後她說:「我要增加他的藥物劑量,他完全失控了。」
我對興奮劑類藥物仍然了解不多,但我知道,更多的藥物並不是解決湯米學習和行為問題的答案。
「米勒太太,我能聽出來您現在感到很挫敗,但其實您和湯米還有很多其他選擇。為什麼不來學校參加一次會議,我們可以一起制定一個計劃?」
那週晚些時候,米勒太太來到了學校,而我也有了時間整理一些想法。我在會議開始時,先談論了湯米的優點,讓她以新的角度來看待她的兒子。「湯米非常有幽默感,而且他總是對班上的其他孩子很友善。」
對她兒子這一點的讚揚,很大程度上鋪平了我接下來要提出的建議的道路。
「米勒太太,湯米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孩子,這意味著他有很多想法和可能性。這是他的天賦,但同時也是他需要學會管理的特質。我希望能幫助他學會一些自我管理的技巧,因為無論他是否繼續服用藥物,他都需要學會如何成功地平衡自己的責任。」
我和湯米一起制定了一個四到五項的計劃,他把這些項目放在桌上的資料夾裡。其中幾個需要努力的事情包括:把課堂發放的講義放進筆記本的「筆記」部分,在起身削鉛筆之前至少專心工作十分鐘,還有使用圖表來幫助他為短文的段落進行結構安排。如果他需要提醒來重新集中注意力,我會輕輕敲一下他的椅子,而不是直接叫他的名字。我們幾乎每天都會談論他的進展,我覺得他最終成功的原因是因為他參與了決定自己該做什麼的過程。由於他在這個過程中擁有了自主權,他對這個計劃有了主人翁意識。他媽媽給他的任何物質獎勵都只是次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他逐漸增長的自信和更強的執行功能。湯米的成功讓他的媽媽對他的行為和學業成就有了更好的感覺。但最重要的收穫是湯米開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因為他正在學習如何以更有生產力的方式引導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
找到更好的前進道路
在我所有的大學、研究生學習以及作為特殊教育工作者的多年經歷中,我從未參加過任何深入探討使用興奮劑藥物來提高注意力和控制行為的正反面影響的課程或工作坊。我自己也從未深入研究過這類藥物——當康納短暫服用這些藥物時,我可能讀過藥品說明書,但他並沒有出現問題,所以我的好奇心也就止步於此。然而,在我與之共事的所有老師和心理學家中,興奮劑的使用是廣泛接受的,幾乎像是理所當然,且很少有人質疑。直到我離開公立學校,開始在馬里蘭大學的專業寫作課程中任教時,我才通過閱讀由MIA創始人羅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撰寫的《流行病的解剖》開始真正了解這些藥物的使用問題。
這本書提供了許多我希望在教學時以及當我面臨兒子ADHD診斷時就能了解的信息。例如,重要的是了解長期使用興奮劑通常會影響孩子的自尊,因為他們會認為自己有某種本質上的問題,必須通過藥物來解決。與此同時,沒有證據表明使用興奮劑可以帶來兒童行為的長期改善。雖然興奮劑可以減少老師們所謂的短期「煩人行為」,如敲桌子、分心和課堂干擾,但也沒有證據表明這些藥物能在長期內提高學術成就。惠特克引用的研究者赫伯特·里(Herbert Rie)發現,利他林並沒有改善「學生的詞彙量、閱讀、拼寫或數學能力,反而阻礙了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對我來說,最令人不安的資訊來自惠特克書中比較興奮劑藥物副作用和雙相情感障礙症狀的圖表(編輯註:你可以在此查看該圖表)。當他解釋這些被診斷為其中一種障礙的孩子的數量在現實生活中意味著什麼時,警鐘在我腦海中響起:「如果一個社會給350萬兒童和青少年處方興奮劑,應預料到會因此產生40萬名雙相情感障礙的青少年。」而一旦被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這很可能會導致終身的精神藥物使用。
即便有這麼多關於興奮劑藥物對兒童有害影響的驚人發現,許多醫生仍然習慣性地開出這些處方,且公眾普遍認為這些藥物基本上無害。我認為,我們需要解決這些藥物的隨意使用問題,例如,為教師提供更多在職培訓,介紹替代的行為管理方法。教師還需要對興奮劑的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這樣他們才能明白這種過於方便的化學解決方案的陷阱。教師培訓計劃應該包含一個單元,專門講解使用興奮劑藥物的危害。而最重要的是,當家長面臨給孩子使用藥物的選擇時,他們應該享有充分知情同意的權利。我相信,如果更多的教師和家長意識到,藥廠所提供的「神奇藥丸」其實更像是毒蘋果,他們會尋找更好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