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與美國對「注意力缺陷多動症」(ADHD)的不同處理方式》
作者:雷德蒙·歐漢隆,哲學博士
2017年6月24日
自從David Cohen(2013年)以及Conrad和Bergey(2014年)研究法國對待ADHD治療的方式以來,法國的情況發生了快速的變化。現在看來,美國的心理健康方法正在迅速在這個曾經以其偉大的、或許過於複雜的(拉康等)精神分析傳統自豪的國家站穩腳跟。法國過去也有一種全面的心理社會傳統,特別是在處理兒童心理困擾時。
正如Conrad和Bergey所言,美國的行為規範如今被輸出到全球,壓制了那些在像法國這樣的不同文化中更有意義的干預措施,法國的多元因素視角曾經是主流。事實上,當Ciba-Geigy公司在1985年因銷量低迷而放棄其利他林(Ritalin)的許可時,這已經充分說明了法國對心理困擾的態度,以及法國普遍反對對兒童進行藥物治療的立場。尤其有趣的是,法國作為一個主要的藥物消費國,傳統上一直不願意給孩子用藥。或者曾經是這樣的。現在,情況正在迅速改變,這是Conrad和Bergey在2014年研究法國當前兒童ADHD治療時所未察覺到的。詳細說明這一變化之前,我們可以對美國和法國對待ADHD症狀和治療的標準做一個比較。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英美生物醫學精神病學(BMP)在哲學上是多麼的匱乏,BMP假定生物學是生長和行為的唯一決定因素;一個小孩生活在真空中,通過無性出生進入世界,然後不受貧困、不平等、忽視、營養不足、虐待、失落和分離等小事的影響。大多數美國兒童精神科醫生認為ADHD是單一原因的疾病,即孩子大腦中的一種生物疾病,需要生物學治療,最好是用利他林(Ritalin)或阿得拉(Adderall)等興奮劑來治療——這樣就可以避免創造性思考、反思背景以及探索其他可能的病因。
這樣的精神科醫生可能會感到驚訝的是,ADHD並非像他們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固定的、普遍接受的“神經發育”生物疾病類別。這在法國並不是如此,當地精神科醫生傾向於探索孩子的潛在心理社會背景,以整體的、如今已經過時的生物-社會-心理方式治療注意力和多動問題——通過心理治療或家庭輔導來處理兒童的行為問題,而不是用藥物治療。法國精神科醫生更傾向於假設或尋找導致孩子困擾的潛在問題,而這些問題不在孩子的大腦裡,而是在孩子的社會背景中。這與美國臨床醫生的看法截然不同,後者傾向於自動將所有症狀歸因於孩子大腦中的生物缺陷或功能障礙。
或許這是一個幻想,但法國中學中哲學的強大存在(而不是生物醫學精神病學!)可能是促成這裡傳統精神病學採取整體、多元因素方法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對英美生物醫學精神病學研究中的完全缺乏反思感到不斷驚訝,即使是在頂級研究中:《柳葉刀精神病學》最近一項關於ADHD的虛浮“巨型分析”或帕羅克西汀(Paxil)329號研究的智力貧乏會讓大多數法國專業人士感到震驚。
生物醫學精神病學是一個缺乏思想的領域,迫切需要具備哲學思維的從業者來提出大問題,洞穿花言巧語和循環思維。像這些研究為真正的科學家和哲學家提供了容易攻擊的靶子,他們鄙視那些被當作精神病學研究的東西。順便說一句,我經常想,為什麼我們沒有官方的醫學或精神病學哲學家。由於精神病學訓練本身幾乎保證了對複雜存在問題的簡單藥物解決方案,任何激進的跨學科改革都會讓生物醫學精神病學的基礎崩塌嗎?或者是否有數十億美元的利益像惠氏疫苗試驗那樣岌岌可危,以至於真相可能會破壞大型製藥公司帶來的繁榮,甚至引發經濟衰退?(在法國,科盧什曾經說過,電視上從來看不到真相,因為觀眾太多!)
正如我們所知,MIA論壇和英國批判精神病學網絡有很多富有思想的激進作家,但我們需要更多精通其他學科的人,比如Pat Bracken、David Cohen、James Davies、Jo Moncrieff、Phil Thomas、Sami Timimi、Manuel Vallée和Ben Goldacre,他在媒體中有強大的影響力,並且受過正統的哲學訓練。讓我們希望,倫敦國王學院的醫學與精神病學哲學碩士學位課程和去年我們一些人參與的劍橋精神病學哲學會議是這方面的好兆頭。
法國的精神疾病分類
傳統上,法國的兒童精神科醫師並未受制於那種滋生偽科學、且心無旁騖地推崇《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之超消費主義、反哲學文化。他們使用的是《法國兒童及青少年精神障礙分類》(CFTMEA),該系統首次於1983年發佈,並在1988年和2000年進行了更新。根據奧克蘭大學社會學家曼努埃爾·瓦耶(Manuel Vallée)的說法,法國精神醫學聯合會於1980年開發了這一更專注於兒童的分類系統,作為對DSM-III影響的抗衡行動。
與DSM不同的是,CFTMEA專注於識別和解決兒童症狀的潛在心理社會原因,而不是尋找最“有效”的——即最具強制性和最有利可圖的——藥物方法來忽視和壓制症狀。這種做法的結果是,直到最近,相對較少的法國兒童符合注意力缺陷多動症(ADHD)的診斷標準,該標準定義嚴謹,不受公關壓力和像喬·比德曼(Joe Biederman)這些腐敗但著名的醫學專家的研究左右。法國的臨床醫師並不急於將正常的兒童活動和充滿活力、衝動的行為病理化。反觀美國,1994年版的DSM-IV則對潛在原因漠不關心,允許臨床醫師隨時開處方,導致未來二十年間ADHD診斷和興奮劑處方數量的指數增長。
然而,當時是那樣,如今情況變化迅速,法國正朝著純粹的生物學兒童精神病學方向發展,以至於法國精神病監督機構——《人權公民委員會》(CCDH)警告說,為數十萬法國學童開立利他林(Ritalin)的處方是一場可能引發公共健康新醜聞的悲劇。該組織領導層的擔憂在於,法國官方機構《高等衛生管理局》(HAS)發布的針對全科醫師和醫療人員的良好實踐建議與《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NIMH)的建議如出一轍,完全遵循生物醫學和大型製藥公司的教條,從而促成了過去八年中法國利他林處方量高達70-80%的大幅增長。
法國ADHD的發病率
在法國,確定ADHD的發病率極其困難,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討論過的那樣,精神疾病的診斷可靠性分數著名地低,尤其是ADHD的診斷。2000年,Scahill和Schwab-Stone發現ADHD發病率存在令人震驚的變異性,範圍從2%到17%不等,這表明這些估計值之間的巨大差異可能是由於信息提供者、抽樣或數據收集方法的選擇,但最有可能是由於ADHD定義過於寬鬆。最近,法國《高等衛生管理局》(HAS)認為法國ADHD的發病率在4%到6%之間,約為美國發病率的一半,但其他法國研究講述了另一個故事,這進一步凸顯了ADHD診斷的高度主觀性。
著名的獨立研究機構INSERM在2002年發現,法國ADHD的診斷率在兒童和青少年人群中從0.4%到16%不等。換句話說,對於一些專業研究人員來說,每千名兒童中有4名“患有”ADHD,而對於其他人來說,這一數字是前者的40倍——每千名兒童中有160名!現在,如果一個像INSERM這樣的重要研究機構在診斷糖尿病時出現如此大的變異,我們會賦予這一診斷多大的可信度?我們難道不會得出結論,要麼它無法做簡單的算術,要麼診斷本身就像唐納德·特朗普一樣模糊?
風險
在美國,對於精神藥物的風險評估和監管極其鬆散,甚至可以說是可恥的。但即便是高度受利益影響的FDA(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最終也發佈了關於服用哌甲酯(methylphenidate)的黑框警告,指出其存在多重風險,包括藥物濫用、精神病發作、攻擊性、自殺、心臟問題和生長激素損傷。然而,這似乎對處方行為和消費者需求幾乎沒有影響。相比之下,法國法律對這些風險更加重視,將初次開立利他林(Ritalin)處方的權利限制在神經科、精神科和兒科專家之內。
然而,最近的證據表明,根據法國藥品安全局(L’Agence Française de Sécurité du Médicament)的說法,法國也正在逐漸走向美國的方向。該法規已經被常規違反,超過10%的處方現在是由全科醫生非法開立的。當我們了解到這些醫生不僅沒有受到衛生部門和官方機構的懲罰,反而受到《高等衛生管理局》(HAS)的公開鼓勵去為這種“疾病”開藥——其存在本身就極具爭議時,法國精神病學的范式轉變變得更加明顯。
傳統上,法國精神科醫生將藥物視為治療兒童的最後手段,優先考慮ADHD類似症狀的其他潛在病因,如心理社會背景、睡眠問題和營養狀況——這在全球充斥著通信技術、信息過載和人造色素、糖分、危險添加劑、防腐劑和過敏原泛濫的垃圾食品文化中顯得相當合理。畢竟,在某些情況下,通過飲食干預可以在一夜之間消除孩子的“ADHD類似”症狀!
結構與紀律
根據帕梅拉·德魯克曼(Pamela Druckerman)的書《法國媽媽育兒經》(Bringing Up Bébé),法國孩子通常比美國孩子表現得更好。這本書基於她在兩國的生活經驗,強調了它們截然不同的育兒方式。這無疑是因為在法國文化中,結構和紀律的概念非常重要,尤其是在1789年之後。雖然這種概念有時會被中央集權的反動勢力用來壓制差異和少數群體,但在養育小孩時,它對安全感的培養至關重要。
在法國的學校和家庭裡,飯點時間嚴格規定,隨意的零食吃得很少,因此孩子們沒有自動享有隨時索取含糖食品和飲料的權利;攻擊性、消費主義的個人主義不受鼓勵!法國父母掌控全局,並且得到了崇尚紀律文化的支持,這在兒童養育上比美國要明顯得多。對他們來說,就像彼得·布雷金(Peter Breggin)所言,無條件的愛,結合一致性以及明確且堅持執行的界限,能讓孩子感到安全、穩定、自信——用溫尼科特的話來說,就是被“很好地抱住”——這樣他們才能更容易地分離、實現自主並發現自己的創造力。(南錫大學(U. Nancy)的埃夫林·西蒙-佩澤什尼亞(Evelyne Simon-Pezeshknia)於2011年撰寫的博士論文是對比ADHD在法國和英美精神病學界至2009年被看待和治療方式的寶貴資訊和反思來源。)
根據溫尼科特(Winnicott)、鮑爾比(Bowlby)、西格爾(Siegel)、肖爾(Schore)等人的研究,我們應該清楚認識到,安全的依附關係比任何藥物都更能幫助孩子實現身心的自我調節。事實上,我相信早期的創傷和依附關係缺陷在成癮以及許多情緒障礙,也即“精神疾病”,特別是在ADHD中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任何與兒童一起工作的現代優秀治療師,特別是那些依附理論的專家,都知道紀律、界限和無條件的愛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而不是藥物。當我們審視傳統的法國ADHD處理方式時,我們可以理解將最低限度的反思和整體的系統思維引入精神病學實踐的好處,但也只能對其逐漸被削弱表示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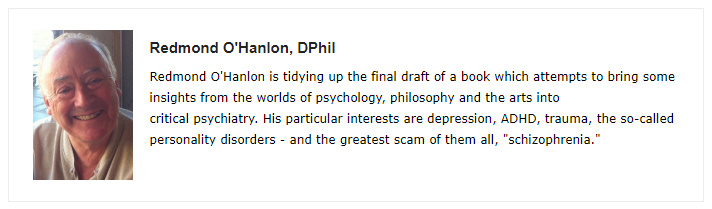
雷德蒙·奧漢倫目前正在整理一本書的最後稿件,該書試圖將心理學、哲學和藝術領域的一些見解引入批判精神病學。他特別感興趣的主題包括抑鬱症、ADHD、創傷、所謂的人格障礙——以及所有這些中最大的騙局:“精神分裂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