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動症:一個毀滅性的精神醫學騙局
作者:Philip Hickey, PhD – 2016年10月30日
引言
今年早些時候,《紐約時報》的調查記者艾倫·施瓦茲(Alan Schwarz)出版了他的最新著作:《多動症國度》(ADHD Nation)。
書封的簡介寫道:
“超過七分之一的美國兒童被診斷為多動症——這是專家認為合適數量的三倍——這意味著數百萬孩子被誤診,並服用像Adderall或Concerta這樣的藥物來治療他們可能並不存在的精神疾病。每年這個數字都在上升。儘管如此,許多專家和製藥公司仍否認有任何值得擔憂的理由。事實上,他們認為成年人和世界其他地區應該擁抱多動症,並且這些藥物將改變他們的生活。
在《多動症國度》中,艾倫·施瓦茲探討了這一文化和醫學現象的根源及其崛起:多動症之父基思·康納斯(Dr. Keith Conners)花了五十年時間推廣像Ritalin這樣的藥物,最終意識到自己在這場‘危及國家安全的災難’中所扮演的角色;一個困擾重重的小女孩和一個勤奮的青少年男孩陷入不斷增長的多動症體系,服用了反效果極其糟糕的藥物;而大型製藥公司則極度過度推廣這一疾病,並通過誤治兒童(現在還包括成年人)賺取了數十億美元。”
對此,誰能反駁呢?但是簡介繼續寫道:
“在證明多動症是真實存在並且在合適的情況下可以用藥物治療的同時,施瓦茲響起了早該拉響的警報,並敦促美國應對這一不斷增長的國家健康危機。”
當然,這正是我們分歧的地方。
當我第一次讀到這個簡介時,我很好奇艾倫·施瓦茲會用什麼樣的論據來支持他關於多動症“真實存在”並且有時需要“用藥物治療”的觀點。讓我們明確“真實”一詞的含義。沒有人否認注意力不集中、多動和衝動可能是實際存在的問題。然而,當前爭論的焦點是,將這些鬆散、定義模糊的問題概念化為一種疾病是否合理。通常,當人們說或寫多動症是真實的時,他們的意思是這些在美國精神病學會手冊(DSM)中列出的問題群是一種真正的、經認證的疾病——就像糖尿病一樣;那些“患有”這種所謂疾病的人必須服用“藥物”,就像糖尿病患者必須服用胰島素一樣。因此,當簡介承諾施瓦茲將證明多動症是一種真正的疾病時,這似乎很重要。正如我之前所說,我對他是否能為這場辯論提供新的見解特別感興趣。
當然,這就是我們分歧的地方。
當我第一次讀到書封上的簡介時,我很好奇艾倫·施瓦茲(Alan Schwarz)會用什麼樣的論據來支持他所主張的多動症是“真實存在的”,並且有時需要“藥物治療”的觀點。讓我們首先明確“真實”這個詞的含義。沒有人否認注意力不集中、多動和衝動可能是真實存在的問題。然而,當前的問題是,將這些鬆散且定義模糊的問題群概念化為一種疾病是否合理。通常當人們說或寫多動症是真實的時,他們的意思是,這些在美國精神病學會手冊(DSM)中列出的問題群是一種真正的、經認證的疾病——就像糖尿病一樣;那些“患有”這種所謂疾病的人必須像糖尿病患者需要服用胰島素一樣服用“藥物”。因此,當簡介承諾施瓦茲將證明多動症是一種真正的疾病時,這似乎很重要。正如我之前所說,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他是否能為這場辯論提供新的見解。
這是引言的開篇。
“注意力缺陷多動症是真實存在的。別讓任何人告訴你不是這樣。
一個在家裡或繁忙街道上瘋狂亂跑的男孩可能會讓自己和他人處於危險之中。一個甚至不能安靜坐兩分鐘來聽老師講課的女孩將無法學習。一個無法集中注意力準確填寫健康保險表格的成年人,將無法應對現代生活的要求。當一個人,不論年齡,這些問題的組合嚴重到足以影響他的日常功能,並且沒有其他合理的解釋時,那麼他很可能患有一種嚴重的疾病,儘管這種疾病仍然有些神秘,醫學界已將其稱為多動症。
沒有人確切知道它的原因。最常被引用的理論是,典型多動症的過度活躍、缺乏專注和衝動性,源於大腦中化學物質和突觸的某種功能失調。一個人的環境顯然也起著作用:混亂的家庭、不靈活的課堂或分心的工作環境都可能引發或加劇症狀。不幸的是,與許多精神疾病(如抑鬱症或焦慮症)一樣,沒有確定的方法可以診斷多動症,沒有血液檢查或CAT掃描可以讓醫生宣佈,‘好了,這就是了’——能做的只有慎重評估這種行為的嚴重程度是否足以診斷。(畢竟,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心或衝動性。)然而,有一點是確定的:多動症沒有治療方法。患有此疾病的人可能會學會適應它,也許藉助藥物的幫助,但年輕和年老的患者通常被告知,他們將一輩子與其‘異常的大腦’相處。”(第1頁)
這就是問題所在。讓我們仔細看看。
“注意力缺陷多動症是真實存在的。別讓任何人告訴你不是這樣。”
“多動症”的真實性與否是整場辯論的根本問題,而從這句開場話來看,很明顯施瓦茲先生並沒有以任何接近於開放心態的方式來探討這個問題,這正是我們期望從一位調查記者那裡得到的。
但情況更糟。
“一個在家裡或繁忙街道上瘋狂亂跑的男孩可能會讓自己和他人處於危險之中。”
施瓦茲先生顯然試圖營造一種印象,即這種行為在“患有多動症”的孩子中相當典型,他同時也指出這些行為是嚴重的。然而,他沒有提到的是,或者說他可能甚至沒有意識到,進行身體危險活動——包括“在過馬路時不看路”——曾經是DSM-III-R(《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修訂版)中多動症的具體標準之一,但在DSM-IV(《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中被弱化為“過度跑跳或攀爬”。而在DSM-5(《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中,“過度”一詞被刪除了。以下是這三個版本中的實際條目:
DSM-III-R(1987年): “(14) 經常進行不考慮後果的身體危險活動(不是為了尋求刺激),例如,不看路就跑進街道。”(第53頁)
DSM-IV(1994年): 在“多動性”子標題下: “(c) 經常在不適當的情況下過度跑跳或攀爬(在青少年或成年人中,可能僅限於主觀上的不安感)。”(第84頁)
DSM-5(2013年): 在“多動性和衝動性”子標題下: “c. 經常在不適當的情況下跑跳或攀爬。(註:在青少年或成年人中,可能僅限於感覺不安。)”(第60頁)
因此,一個在家裡或繁忙街道上瘋狂亂跑的男孩可能在這三個版本中都符合標準,但——這是關鍵點——在後兩個版本中,並不需要如此極端的行為就可以被視為“症狀”。與施瓦茲先生暗示的觀點相反,孩子不需要表現出如此極端或危險的行為來符合美國精神病學會所謂的這種“疾病”的任何標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自1994年以來,對於成年人和青少年,這一項目唯一的要求是他們感到不安!
. . . . . . . . . . . . . . . .
“一個甚至無法安靜坐兩分鐘聽老師講課的女孩將無法學習。”
艾倫·施瓦茲(Alan Schwarz)——或者其他人——如何得出一個不專心聽老師講課的女孩就無法集中注意力的結論?這是一個無效的推論,但在精神病學中卻是常見的做法。
. . . . . . . . . . . . . . . .
“當一個人在任何年齡層都經歷這些困難的組合——嚴重到影響他的日常功能——且沒有其他合理的解釋時,那麼他很可能患有一種嚴重但仍有些神秘的疾病,醫學將其稱為多動症(ADHD)。”
這又是精神病學中的標準話術:問題在於“沒有其他合理的解釋”這句話中。
任何有過哪怕最微小的與兒童和家庭共事經驗的人都可以證明,只要你願意去尋找,總會有其他心理社會因素的解釋。然而,現實是,在精神病學的實踐中,這些替代解釋幾乎從未被尋求過。
而這些解釋之所以沒有被尋求,是因為精神病學已經有效地關閉了這類討論的大門。在精神病學的框架中,如果一個孩子(或成年人)符合DSM中列出的那些任意且本質上模糊的標準,那麼他就患有一種被稱為多動症的大腦疾病。因此,尋找心理社會解釋的想法不僅不存在,而且在精神病學內部會被認為是荒謬的。
在真正的醫學中,如果一個人患有肺炎,那麼這就是他持續咳嗽、咳出惡心痰液和虛弱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醫生去尋找其他心理社會解釋的想法是毫無意義的。同樣,精神科醫生緊密依附於他們虛假的疾病觀點,並不會去尋找他們遇到的問題的普通人類解釋。當然,精神病學與真正醫學的區別在於,後者的診斷確實是呈現問題的真正解釋。而在精神病學中,這些“診斷”只是精神科醫生給這些模糊問題群所貼的標籤,並沒有任何解釋價值。
為了證明這一點,請考慮以下兩段假設的對話。
客戶的家長: 為什麼我兒子這麼容易分心?為什麼他在學校作業中犯了這麼多錯誤?為什麼當我和他說話時他不聽?為什麼他這麼沒有條理?
精神科醫生: 因為他患有一種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動症的疾病。
家長: 你怎麼知道他患有這種病?
精神科醫生: 因為他很容易分心,做作業時犯了很多錯誤,當你和他說話時他不聽,並且很沒有條理。
關鍵問題在於,在精神病學中,對於“疾病”的唯一證據就是它所聲稱要解釋的行為。換句話說:你的兒子之所以分心,是因為他分心。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真正的醫學中類似的對話。
患者: 為什麼我這麼疲倦?為什麼我的體溫會突然升高?為什麼我咳出的痰這麼難看?
醫生: 因為你患有肺炎。
患者: 你怎麼知道我得了肺炎?
醫生: 因為我可以通過聽診器聽到特徵性的聲音;你的胸部X光顯示兩側肺部都有大量積液;痰液實驗室檢測顯示有肺炎球菌;而且你告訴我的一切都與這一診斷相符。如果你願意,我可以給你看X光片。
在這段對話中,沒有任何推理上的循環。肺炎是症狀的原因,並構成了一個真正且有用的解釋。
. . . . . . . . . . . . . . . .
“沒有人確切知道它的成因。”
實際上,很多人知道促使孩子“在家裡或繁忙的街道上瘋狂亂跑”的原因。原因非常簡單,因為在適當的年齡內,他們沒有被灌輸自律和自我控制來避免這種行為。這並不是“有點神秘”的事情。這是父母和祖父母可能從史前時代就一直在處理的問題。其他被稱為多動症行為的問題也是如此,在《DSM》中被誤導地稱為“症狀”。
. . . . . . . . . . . . . . . .
“最常被引用的理論是,典型多動症的過度活躍、缺乏專注和衝動性源於大腦中化學物質和突觸的某種功能失調。”
就在我們以為那個早已被否定的化學失衡騙局即將消失時!施瓦茲先生似乎沒有意識到,目前大多數領先的精神科醫生正在忙於與這一荒謬的觀點保持距離,這一觀點曾經是精神病學騙局的基石數十年。非常著名且備受尊敬的塔夫茨大學精神科醫生羅納德·派斯(Ronald Pies,MD)甚至曾聲稱,精神病學從未推廣過這一騙局——這一主張為學術界虛構的象牙塔增添了一個全新的維度。
然後施瓦茲先生進入了正題:
“很不幸,與許多精神疾病(如抑鬱症或焦慮症)一樣,沒有明確的方法可以診斷多動症,沒有血液檢查或CAT掃描可以讓醫生宣佈,‘好了,這就是了’——唯一能做的就是仔細評估行為的嚴重程度是否值得診斷。(畢竟,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心或衝動。)”
儘管早前的描述模糊不清,儘管施瓦茲先生譴責他所描述的多動症的過度診斷,他顯然是精神病學的一個堅定支持者,認為只要不注意力、衝動性和過度活動達到某種不明確的嚴重程度,就構成了一種疾病。
這是精神病學中的另一個核心謬誤,這個謬誤在DSM的各個版本中一再推廣,也出現在精神病學最權威的支持者的辯護性著作中:如果一個思維、情感或行為的問題達到了某些任意且模糊定義的嚴重性、持續時間或頻率,通過精神病學中某種神秘的過程,它就變成了疾病。即便沒有發現任何器質性病理,這也無關緊要。如果問題足夠嚴重,那麼它就是一種疾病。
這種荒謬的原因在於,在精神病學的診斷框架內,問題的原因是無關緊要的。這正是羅伯特·斯皮策(Robert Spitzer)在其DSM-III和後續版本中所體現的現象學方法的核心點。為什麼一個人表現出某種問題並不重要。如果在“多動症”的情況下,一個孩子不注意力過度、活動過度且衝動,達到了文本中規定的(儘管含糊不清)的程度,那麼他就患有這種疾病。不管這些行為是由於寬鬆的教養、不一致的教養、溺愛的教養、兄弟姐妹的競爭、情感虐待,還是其他原因,都不會影響“診斷”。這與真正的醫學形成了鮮明對比,在真正的醫學中,診斷與原因幾乎是同義的;而在精神病學診斷中,問題的原因是無關緊要的。如果孩子出現了這些行為,不管原因是什麼,那麼他“就患有這種疾病”。實際上,這種“疾病”僅僅是這些模糊定義的問題行為的存在。並不要求存在神經病理學,也沒有證據表明這些行為涉及任何神經病理學。DSM-III 對這種方法的描述是“…關於病因學或病理生理過程的無理論化,除了那些已經被很好確立並因此被納入疾病定義中的疾病。”(第23頁),這並不適用於多動症。
不僅如此,DSM-III-R實際上將這種“無理論化”方法視為一種美德:
“DSM-III和DSM-III-R在病因學方面採取的無理論化方法的主要理由是,病因學理論的納入將成為不同理論取向的臨床醫生使用本手冊的障礙,因為不可能為每種疾病呈現所有合理的病因學理論。”(第23頁)
然而,現實情況是,通過忽視病因學問題,美國精神病學會創造了一個能夠隨意創造“精神障礙”的語境,這些“障礙”可以,實際上也確實迅速轉變為“精神疾病”,而且,正如我們在施瓦茲先生的文字中所見,它們與神經化學失衡相關聯。精神病學方便地拋棄了新診斷必須基於已證實的器質性病理學的觀念。真正的醫生通過艱苦的研究和學習發現新疾病——這通常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精神病學則通過委員會投票隨意創造新疾病,並通過投票確認其本體論的有效性。
幾十年來,精神病學自信地知道很少有人會讀DSM,於是對於缺乏器質性病理學的事實大肆撒謊。他們告訴他們的患者、大眾和媒體一個公然的謊言,稱“化學失衡”存在並且是問題的原因。而最大的謊言是,藥物可以糾正這些不存在的失衡。他們還經常聲稱,他們的“患者”在許多(或許多數)情況下需要終生服藥。在這裡,施瓦茲先生也緊跟他的精神病學導師。
“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的:多動症無法治癒。”
再次注意這種教條式的傲慢。那些不專心、難以控制、違反紀律並且在DSM中被模糊規定為不守規矩的孩子,無法獲得適齡的自律能力!施瓦茲先生怎麼能知道這些?早在1973年,胡西、馬歇爾和根德隆(《從二年級到五年級追蹤五百名兒童的行為障礙患病率研究》,Acta Paedopsychiatrica,39(11),301-309)就顯示出多動性並不是一種跨時間穩定的模式。還有大量可追溯到60年代的研究清楚地表明,習慣性不專心、衝動和極度多動的孩子可以很容易被訓練成為行為更有生產力且干擾性較小的孩子。事實上,在60年代中期之前,根本不需要這些研究,因為家長和教師通常都能成功訓練孩子控制自己的行為,專心於學業和日常任務。實際上,家長和教師都認為這是他們責任的一部分。然而,在1968年,隨著《DSM-II》的出版,精神病學的“頂尖專家”宣佈這些問題行為構成了一種需要專家關注的疾病。這種“疾病”被稱為兒童的過動反應。描述只有四行:
“308.0 兒童(或青少年)的過動反應* 這種疾病的特點是過度活躍、不安、分心和注意力持續時間短,尤其在年幼的孩子中;這種行為通常在青春期減少。”(第50頁)
. . . . . . . . . . . . . . . .
“…年輕和年長的患者通常被告知,他們將一輩子與其異常的大腦打交道。”
儘管幾十年來進行了大量資金充裕且動機強烈的研究,儘管有過無數次熱情洋溢但後來被駁斥的宣稱,仍然沒有一絲證據表明那些被診斷為多動症的人存在任何腦部病理學問題。事實上,無論是DSM的任何一個版本,包括當前的DSM-5,都未曾將任何形式的腦部病理學列為這種所謂疾病的診斷標準之一。DSM-5 確實將多動症歸入神經發育障礙部分,但這只是說明問題的發生是在發育期。並不要求有神經病理學。“神經發育障礙是一組發育期開始的疾病。這些疾病通常早期發作,經常在孩子入學前表現出來,其特徵是發育缺陷,這些缺陷會導致個人、社交、學業或職業功能受損。”(第31頁)將“多動症”描述為神經發育障礙對我來說是一種極具欺騙性的做法,因為大多數人會將“神經發育障礙”解釋為某種神經病理學。美國精神病學會在這裡所做的,是傳達了多動症涉及神經病理學的印象,但並未提供證據來證明這一點。
多動症的“過度診斷”
然後施瓦茲先生轉到他書中的主要主題:多動症被過度診斷。這一主題最近幾年也被許多精神病學家採用,他們試圖拯救自己日益崩潰的行業免受反精神病學的批評。看看施瓦茲先生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
“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對多動症的官方描述,由該領域的頂尖專家編纂,指導全國的醫生,表明這種病症影響約5%的兒童,主要是男孩。大多數專家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基準。
但在現實生活中的美國發生了什麼呢?
美國有15%的孩子——是這個共識估計的三倍——被診斷為多動症。這意味著數百萬的孩子被告知他們的大腦有問題,其中大多數孩子隨後被給予嚴重的藥物治療。全國男孩的診斷率驚人地達到了20%。在像密西西比、南卡羅來納和阿肯色這樣的南方州,這一比例達到了所有男孩的30%,幾乎每三個男孩中就有一個被診斷患有多動症。有些路易斯安那州的縣,三到五年級的男孩中幾乎有一半在服用多動症藥物。
多動症已成為美國醫學中被誤診最多的疾病。
然而,令人沮喪的是,在蓬勃發展的多動症產業複合體中,少有人承認這一現實。許多人都是出於善意——他們看到了在客廳、課堂或診室裡掙扎的孩子,並相信診斷和藥物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其他人的動機則更為混合:有時候教師希望學生不那麼麻煩,家長希望家庭少些嘈雜,而醫生則喜歡穩定的生意。在最惡劣的角落裡,則是那些被製藥公司買通的高知名度的醫生和研究人員,他們從不受監管和魯莽推進的多動症中賺取了數十億美元。”(第2-3頁)
然而施瓦茲先生沒有提到的是,也許他甚至不知道,那些為DSM-5編纂多動症標準的“頂尖專家”中有69%也在接受製藥公司的報酬,這些製藥公司推廣多動症藥物的同時支付了這些專家的費用。
施瓦茲先生似乎也沒有意識到,這些編纂多動症標準的“頂尖專家”逐步放寬了這種所謂疾病的標準。在我早前的文章中列出了DSM-IV(1994年)的放鬆標準。以下是DSM-5(2013年)的放寬標準:
– 對於青少年和成人,注意力不集中“症狀”的要求從六個減少到五個(第59頁)
– 對於青少年和成人,過度活躍/衝動“症狀”的要求也從六個減少到五個(第60頁)
– DSM-IV規定一些多動症的症狀必須在7歲之前出現(第84頁)。DSM-5將這一發病年齡標準放寬至12歲(第60頁)。
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放寬標準都不是基於經驗證據或科學研究,也不可能是。除了DSM中所定義的內容外,根本沒有其他關於多動症的定義。說這些由製藥公司付費的“頂尖專家”比較了“真實的多動症”與DSM中的描述並發現了差異,這是不可能的。沒有“真實的多動症”存在。除了美國精神病學會捏造的定義外,根本沒有其他定義。他們可以,並且確實會隨意改變這些標準。到目前為止,大多數變更都是放寬標準的。
. . . . . . . . . . . . . . . .
這是核心問題。對多動症的過度診斷感到遺憾是一種空洞且徒勞的行為。鑑於以下事實:
– 這些標準極度模糊且主觀,
– 製藥公司在擴大範圍時賺取更多錢,
– 精神病學通過各種途徑分享這些利潤,
– 這些藥物具有成癮性,
– 學校因每個被診斷為多動症的孩子會獲得額外資金,
“診斷”範圍的擴大是不可避免的。這並不是某種意外,也不是製藥公司製造的陰謀,儘管精神病學盡力保持純潔和未受污染。“診斷”範圍的擴大是精神病學有意識且故意創造的怪物的一部分。這是精神病學擴張主義議程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且極大地受益於羅伯特·斯皮策(Robert Spitzer)在DSM-III(1980年)中無理論的現象學方法。儘管事實上,在1980年之前,這種情況已經開始發生。以下是Ullmann和Krasner的《異常行為的心理學方法》(第二版,1975年)中的一段話:
“對於那些被標籤為‘多動症’的兒童的治療,在心理學和小兒科領域引發了進一步的爭議……藥物治療,尤其是像苯丙胺這樣的興奮劑,已成為流行的治療方法,在某些學區,這一比例高達所有學生的10%……”(第496頁)
即便在那時,四十一年前,也有明確的反對聲音:
“這個標籤加上藥物治療將孩子歸入精神病或病人的範疇,並隨之帶來社會和自我標籤的影響……藥物的使用增強了對外部因素的效能信念,而不是將改變歸因於自己的努力(這是兒童自我控制能力發展以及教師責任感中的重要元素)。”(同上,第497頁)
還應注意到,標準的放寬並不限於“多動症”。DSM-5還放寬了APA對精神障礙的定義,有效地擴大了所有所謂診斷的範圍。
DSM-IV(1994年)對精神疾病的定義是:
“……在個體中出現的臨床上顯著的行為或心理綜合症或模式,並且與當前的痛苦(例如,痛苦的症狀)或功能殘障(即一個或多個重要功能領域的受損)相關,或與顯著增加的死亡、痛苦、殘障或重要自由喪失的風險相關。此外,這種綜合症或模式不應僅僅是對特定事件(例如親人的死亡)作出的可預期和文化認可的反應。無論其原始原因如何,該綜合症目前必須被認為是個體行為、心理或生物功能失調的表現。除非偏離行為(例如政治、宗教或性行為)或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衝突是個體功能失調的症狀,否則這些行為或衝突不能被視為精神疾病。”(第21-22頁)
這一定義,我認為可以準確地概括為:任何顯著的思維、情感和/或行為問題。實際上,幾乎很難想像有任何顯著的思維、情感和/或行為問題不在DSM中列出。
DSM-5(2013年)對精神疾病的定義與上述定義相似,但包含更多語言,並且對定義進行了一項重大的放寬。為了讓讀者自行判斷,以下是DSM-5的定義:
“精神疾病是一種綜合症,表現為個體認知、情緒調節或行為的臨床上顯著的紊亂,反映了精神功能背後的心理、生物或發育過程的失調。精神疾病通常與社會、職業或其他重要活動中的顯著痛苦或殘障相關。對於常見壓力源或失落(如親人去世)的可預期或文化認可的反應不屬於精神疾病。社會偏離行為(如政治、宗教或性行為)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衝突,除非這些偏離或衝突是個體功能失調的結果,否則不屬於精神疾病。”(第20頁)【強調字體為作者所加】
**第四行的“通常”一詞大大擴展了精神病學“診斷”的潛在範圍。可以說,它的範圍如此廣泛,甚至可以涵蓋整個人口。**重點是,在DSM-IV中,問題必須達到一定程度的顯著性或嚴重性。但在DSM-5中,這一要求實際上被取消了。誠然,兩種說法都很模糊,但DSM-IV要求必須有痛苦或殘障的存在,顯然比DSM-5中的“通常存在痛苦或殘障”更為嚴格。實際上,嚴重性門檻已被放棄,這明顯為臨床醫生提供了一個空間,讓他們可以將“診斷”分配給症狀越來越輕微的個體。而且需要強調的是,這一變化並不是基於任何科學信息或發現。這一變化僅僅是美國精神病學會的決策,旨在擴大他們所謂的疾病的患病率,幾乎涵蓋了地球上的每個人。
此外,這並不是一個無關痛癢的問題,它已經在“多動症”的案例中實施了。將DSM-IV與DSM-5中的多動症嚴重性標準進行比較:
DSM-IV:
“D. 必須有明確的證據表明在社會、學業或職業功能中存在臨床上顯著的損害。”(第84頁)【強調字體為作者所加】
DSM-5:
“D. 有明確證據表明,這些症狀干擾或降低了社會、學業或職業功能的質量。”(第60頁)
在這裡再次強調,兩種說法都很模糊,但“顯著損害”顯然是一個比“干擾或降低質量”更為嚴格的標準。
鑒於所有這些考慮,極難避免得出結論:美國精神病學會不僅支持這種所謂診斷的廣泛擴展,還積極追求並推動這種擴展已經有數十年之久。
結論
施瓦茲先生在揭露製藥公司的戰術和策略方面做得很好。儘管這個故事中的許多內容早已廣為人知,且已經被多次討論過,但他以詳細且易讀的形式展現了這場騙局。他還探討了家長們推動將他們的孩子“診斷”並讓其服藥的問題,以及人們確實會對這些藥物上癮的無可否認的事實。他還揭露了CHADD(注意力缺陷障礙兒童和成人組織)與製藥公司之間的聯繫。
或許現在他可以關注一個更大的騙局:精神病學對每一個思維、情感和/或行為問題的虛假和具破壞性的醫學化,包括兒童的注意力不集中、衝動以及普遍的缺乏紀律。
製藥公司確實使用非常可疑的方法推銷他們的產品。但他們不可能賣出一張利他林或其他任何精神藥物的處方,若沒有精神病學虛假的、自我服務的“診斷”。而他們也無法將銷量推至如此之高,若沒有精神病學蓄意提供的放鬆“診斷”標準的協助。若不願同時將批評指向DSM中同樣膚淺的“症狀列表”,那麼抱怨草率填寫的簡單檢查表是空談,因為這些檢查表只是“症狀列表”的鏡像。
精神病學只不過是合法化的藥物推銷。他們所謂的分類法沒有一絲智識或科學上的有效性。他們編造這些所謂的疾病來擴大他們的領域,然後再放寬標準進一步擴大。
在醫療護理的幌子下,他們經常剝奪了人們的能力感、尊嚴,並在許多情況下,剝奪了人們的生命。他們極大地破壞了“通過紀律性努力獲得成功”的概念,並將數百萬人困在他們不斷擴展的藥物依賴和自我懷疑的網絡中。他們並不是施瓦茲先生所描述的那樣,是真正疾病的專業編纂者。相反,他們是推銷藥物的江湖術士和騙子,系統且故意地欺騙了他們的客戶和公眾,以提升他們自己的聲望和收入。
如果有任何一個話題值得深入調查報導,那就是精神病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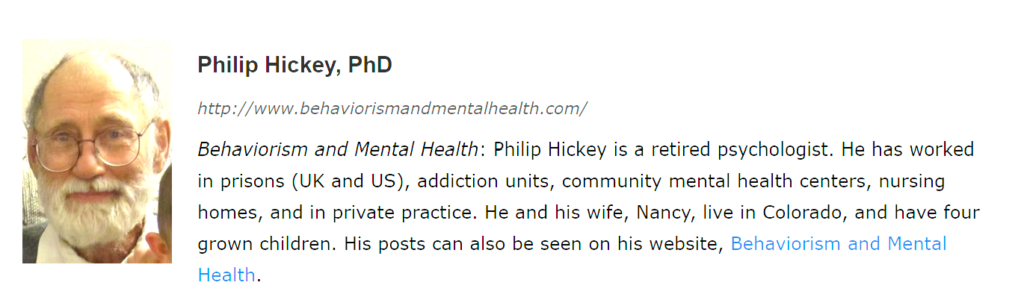
http://www.behaviorismandmentalhealth.com/
行為主義與心理健康:Philip Hickey 是一位退休的心理學家。他曾在英國和美國的監獄、成癮治療單位、社區心理健康中心、療養院以及私人診所工作。他與妻子南希(Nancy)住在科羅拉多州,育有四個已成年的孩子。他的文章也可以在他自己的网站“行為主義與心理健康”上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