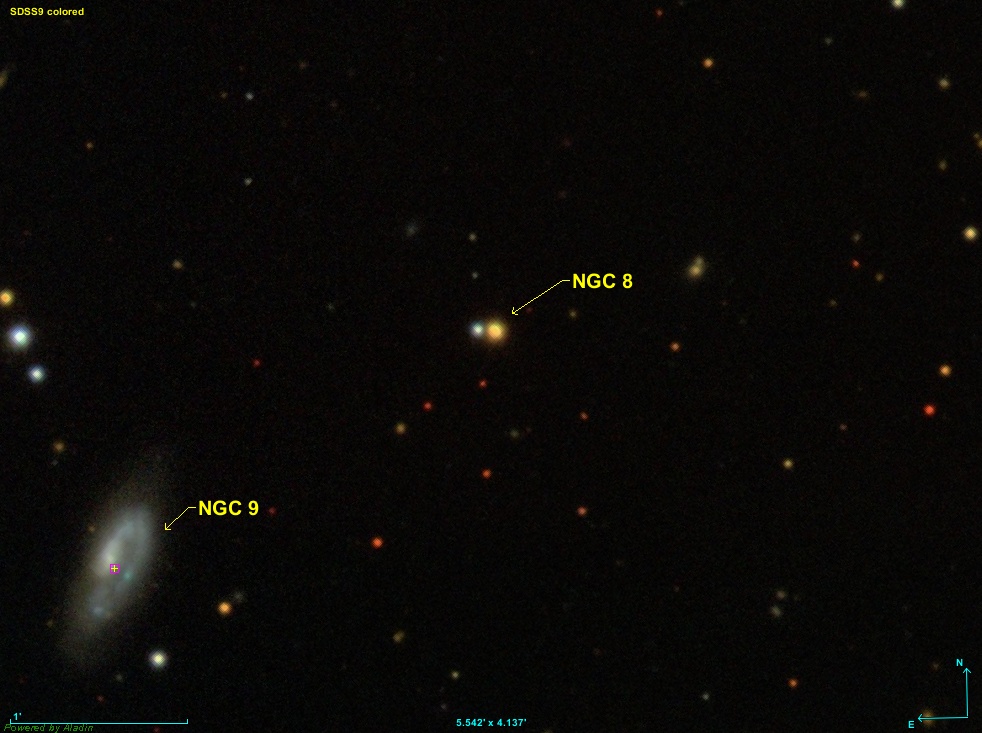Finding One’s Way Through Withdrawal
詹妮弗·霍尼格-2021 年 1 月 10 日
處方者被教導開出精神科藥物,但他們通常沒有接受過關於停止使用這些藥物對患者的影響的良好教育。當患者尋求停止服藥時,他們的開藥者可能無法提供幫助。患者有單獨戒斷的風險。
退出,終止任何類型的精神科藥物的過程,可能是一次平靜的經歷或令人痛苦的經歷,或者介於兩者之間。當人們因戒斷而經歷一系列影響時,有些人將他們的反應稱為“戒斷綜合症”。與退出的概念一樣,該術語沒有單一的表示,而是涵蓋了一系列經驗。
由於開藥者基本上沒有參與關於退出的討論,因此有關此主題的討論已被在線社區所吸引。正如研究人員Peter C. Groot 和 Jim van Os最近所描述的那樣,這是一個許多人參與並從中獲得援助的世界,但它仍然與主流醫學和精神病學在很大程度上分離。
個人討論戒斷的強大在線論壇與有資格的精神病學領域平行存在,儘管其擁有豐富的經驗和信息,但對其影響力不足。與此同時,在患者退出藥物治療時未能跟隨患者的處方者失去了從患者經驗中學習的機會。這些參與者並行地繼續他們的離散角色——一個開處方,一個響應——沒有一個通知另一個。
關於戒斷援助的在線對話揭示了大量尋求停止精神科藥物幫助的人以及現在存在的關於如何最好(或更好)這樣做的大量信息。
除了在線領域之外,對這些數據和實用信息的總體認識不足,阻礙了已建立的治療社區準確評估藥物治療的價值和最好地幫助患者。傳統的護理人員通常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興趣退出,如何協助退出,或者可能有多困難。在線提供的信息必須告知醫生。
該反饋必須首先影響開處方的決定,並且正如本系列後面討論的那樣,向正在考慮用藥的患者提供知情同意。多年來,傳統精神病學的批評者一直在提出這些論點。現在他們轉向撤軍問題,並看到同樣迫切需要改革。
退出:一個緊迫的問題
許多美國人開出的精神科藥物可能會在某個時候尋求停止這種治療。2018 年,美國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接受了精神科藥物治療。而且,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精神疾病的診斷和精神科處方藥的使用均有所增加。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服用精神科藥物的人會尋求停止這種治療。我們還缺乏關於有多少人考慮過退出或有多少人與他們的開藥者提出這個問題的匯總數據。然而,例如,在一項針對精神病患者的研究中,研究人員觀察到人們“經常想要減少劑量或停止”他們的抗精神病藥物。大量在線尋求幫助的人也表明迫切需要有關退出的信息。
此外,人們引用作為停藥基礎的大量原因表明,在某些時候戒斷可能是許多精神科藥物治療的目標。這些包括:
- 擔心副作用,包括體重增加和性功能障礙;
- 擔心懷孕期間服藥;
- 一種情緒平淡的感覺;
- 擔心藥物的長期影響;
- 停止服用藥片的願望;
- 無法接觸到專家;
- 處方者和患者之間缺乏治療關係;
- 物質使用障礙;
- 對藥物的消極態度;
- 相信一個人沒有需要繼續用藥治療的情緒問題。
這一系列的擔憂表明,有一大群人可能對退出有疑問。
許多試圖戒斷的人會受到不利影響
很大一部分試圖戒斷精神科藥物的人會出現戒斷症狀。現在的數據揭示了這些症狀的發生率和性質。
James Davies 和 John Read的 2019 年對抗抑鬱藥物戒斷研究的回顧記錄了 27% 至 86% 的個體的影響,並具有加權平均值(即根據每個數據點的相對重要性分配權重的平均值) 56%。同樣,2020 年對口服抗精神病藥物戒斷的薈萃分析發現,49% 的人在突然停藥後出現症狀,而在繼續服藥的對照組中,這一比例為 11%。
即使停藥是逐漸的,停藥效果也可能很明顯。2020 年,Fiametta Cosci 和 Guy Chouinard記錄了多種藥物的戒斷綜合徵,包括苯二氮卓類藥物、抗抑鬱藥、抗精神病藥、鋰和情緒穩定劑。即使緩慢減量,每類藥物都可能導致戒斷綜合徵和反彈(主要症狀的回歸,雖然持續時間短且可逆,但通常比治療前強度更大)。
正如在線論壇 Surviving Antidepressants 的創始人Adele Framer最近觀察到的那樣,“每個長期服用精神科藥物的人都有出現戒斷綜合徵的風險。”
退出的潛在困難很多而且很嚴重
與每種精神科藥物相關的戒斷症狀的正式編目是不完整的。David Cohen 和 Alexander Recalt最近觀察到,戒斷效應的研究不足。“[N] 對可能在減少劑量或停止使用規定的精神藥物後出現的生理和心理現像沒有達成共識,但《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連續版本中的定義除外。”
儘管如此,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症狀與特定的藥物類別有關。例如,停用抗抑鬱藥,即使逐漸減量,也可能導致“焦慮、易怒、激動、煩躁、失眠、疲勞、震顫、出汗、類似休克的感覺(“腦震盪”)、感覺異常(“針扎”) 、眩暈、頭暈、噁心、嘔吐、意識模糊和注意力下降。” 苯二氮卓類藥物的戒斷可能會引發一些相同的症狀以及其他症狀,例如耳鳴、四肢麻木、肌肉抽搐和腸易激綜合徵。
影響可能很嚴重。Davies 和 Read的 2019 年審查發現,使用加權平均值作為衡量標準,46% 的病例停用抗抑鬱藥會產生嚴重影響。Cosci 和 Chouinard最近警告說,在停用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製劑 (SSRIs)、血清素和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製劑 (SNRIs) 和抗精神病藥物後,會出現持續的戒斷後疾病——長期、嚴重、可能不可逆的症狀。
這些結果可以產生幾乎存在的效果。正如一個人解釋的那樣:“這種退出過程正在慢慢剝奪我對自己和生活的一切信念。“我”的一部分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了,讓我完全沒有任何作為某人的感覺。”
正如Groot 和 van Os所強調的,試圖停止服用精神科藥物的患者通常會因為戒斷的強烈影響而失敗。《紐約時報》引用了精神藥物使用者面臨嚴重戒斷症狀的研究,以至於在一項研究中,近一半試圖戒菸的人因為這些症狀而無法戒菸。
退出背後的科學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
大腦對各種精神科藥物的適應解釋了為什麼戒斷會成為一個問題。在《流行病解剖》一書中,羅伯特·惠特克解釋說,大腦通過“一系列補償性適應”對精神藥物的引入做出反應。具體的適應取決於藥物。
例如,一種抗精神病藥會阻斷神經遞質,其作用是將脈衝從一個神經細胞發送到另一個神經細胞。當一個人接受抗精神病藥時,大腦會通過增加神經遞質的產生和接受性來適應。當一個人服用一種會增加神經遞質水平的抗抑鬱藥時,大腦會適應這種增加。同樣,苯二氮卓類藥物通過放大一種抑制大腦活動的神經遞質(稱為 GABA)起作用。大腦通過減少 GABA 輸出和 GABA 受體密度來適應。使用這些類型的藥物以及其他類別的藥物,大腦會改變其功能以對抗藥物的作用。
停藥後麻煩就來了。由於其新的異常神經功能現在已經根深蒂固,大腦無法切換回其原始機制以響應中斷。例如,對於使用鎮靜劑治療的人,當它被撤回時,適應的、加速的大腦保持在那個高度的狀態,沒有控制機制。
“該系統現在嚴重失衡……退出藥物的患者會出現奇怪的抽搐、激動和其他運動異常[,]精神病復發或惡化。” 同樣,當停用 SSRIs 時,會出現不平衡,因為大腦不再釋放正常量的血清素,也沒有足夠的受體來吸收釋放的少量血清素。當苯二氮卓類藥物被停用時,大腦會處於無法抗拒的過度活躍狀態。在所有這些例子中,結果可能是戒斷症狀。
儘管人們對戒斷效應背後的科學了解越來越多,但這些問題往往未被更大的醫學界承認。
處方者聽不到病人的聲音
患者想退出時可能得不到開藥者的支持
由於各種原因,個人在考慮和尋求撤藥時可能無法獲得開藥者的幫助。他們可能會發現他們的開藥者不會支持停藥。處方者可能會鼓勵患者將一種藥物換成另一種藥物,而不是停藥。臨床醫生可能認為該人患有需要持續治療的疾病,或者停藥會帶來自身的困難。
患者可能首先害怕向他們的臨床醫生提出這個問題。有些人可能擔心開藥者可能會使用強製手段來強制服藥。而且,事實上,一些開藥者明確威脅說,如果人們不按照開藥者的意願行事,他們就會以民事方式對他們實施犯罪。
儘管存在這些障礙,許多患者並沒有放棄戒藥的願望。
處方者缺乏關於撤藥的專業知識
即使開處方者願意與希望退出的患者一起工作,許多人仍缺乏幫助患者的專業知識。大多數人從他們的初級保健提供者那裡獲得精神科藥物。在美國,幾乎五分之四的精神藥物處方由非精神科醫生開具。這是驚人的。這些臨床醫生既沒有關於精神科藥物的專業知識,也沒有時間專注於對戒斷的仔細監督。
在Rethinking Psychiatric Drugs: A Guide for Informed Consent中,精神病學家 Grace E. Jackson 引用了1997 年英國對 100 名全科醫生 (GP) 的調查,該調查發現只有 30% 的全科醫生“對抗抑鬱藥停藥綜合徵有信心”,而只有 51 % 總是或通常建議患者有關藥物戒斷的影響。此外,只有 42% 的 GP 有直接治療與 SSRI 相關的戒斷患者的經驗。只有 6% 的 GP 對停用單胺氧化酶抑製劑 (MAOI) 的患者有過這種經驗,而只有 38% 的 GP 對三環類抗抑鬱藥( TCA) 有過這種經驗。
即使是精神科醫生也可能不擅長幫助人們戒毒。同一項英國調查還詢問了 100 名精神科醫生:只有 72% 的人“對抗抑鬱藥停藥綜合徵有信心”,只有 52% 的人總是或通常建議患者戒毒。雷切爾·阿維夫(Rachel Aviv)在《紐約客》( The New Yorker )上報導,講述了她與杜克大學精神病學名譽教授艾倫·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的談話,他在 1994 年擔任第四版DSM工作組的主席:
[他]告訴我,該領域忽視瞭如何讓患者戒毒的問題——這種做法被稱為“取消處方”。他說:“與開處方相比,取消處方需要患者更多的技能、時間、承諾和知識。
實際效果可能是戲劇性的。Adele Framer描述了她如何拜訪了 50 多名精神科醫生,試圖找到一位了解抗抑鬱藥戒斷的人。
因為在許多情況下,處方者在戒斷期間沒有給他們的患者提供建議,他們沒有獲得關於戒斷效果的經驗知識,也沒有通過經驗教育自己。這導致了另一個問題。不僅處方者缺乏知識,而且他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東西。正如傑克遜在《重新思考精神病藥物:知情同意指南》中所觀察到的那樣,“許多醫生堅持以空洞但方便的證據為食,對他們職業營養不良的跡象視而不見。”
外部權威並不能替代缺乏經驗知識
處方者並沒有彌補他們在其他一些知識庫方面缺乏實踐經驗。精神科醫生可能會接受整個正規教育,但不會了解戒斷。正如精神病學家馬克霍洛維茨在 2019 年評論的那樣,“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抗抑鬱藥的戒斷症狀,不是在醫學院,也不是在我的精神病學培訓中。” 精神科醫生Vivek Datta提到他的訓練,更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不知道如何停止這些藥物。”
此外,製藥公司和美國政府都沒有向精神科醫生提供準確的戒斷信息的一貫歷史。正如《紐約時報》記者所觀察到的那樣,“戒毒從來不是製藥商或政府監管機構關注的焦點,他們認為抗抑鬱藥不會上癮,而且弊大於利。”
專業文獻並沒有填補關於戒斷知識的空白。Rachel Aviv報告了有關退出經驗的重要信息與有限的已發表文件之間的差異。她引用精神病學家和研究員大衛泰勒的話說,如果他自己沒有經歷過抗抑鬱藥的戒斷,“’我想我會被標准文本所推銷。’ 但是,他說,“體驗與頁面上的內容非常不同。”
阿維夫為文學的匱乏提供了一個理由。在描述對抗抑鬱藥戒斷進行長期研究的著名精神病學教授Giovanni Fava的經歷時,她指出 Fava 一直在努力發表他的研究。格魯特和範奧斯總結了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戒斷問題在學術精神病學中並不被認為是一個重要問題。”
今天,就相關文獻正在緩慢傳播的程度而言,開處方的人可能根本沒有閱讀它。Framer最近認為,“有數百篇關於抗抑鬱藥戒斷的論文。大多數臨床醫生、大多數從業者——當然不是你的全科醫生——不閱讀這些論文。” 克里斯托弗·萊恩教授建議,一種解釋是,戒斷研究可能會在大量其他文章中丟失,尤其是那些關於藥物功效的文章。
一家主流期刊承認這種未能諮詢精神科藥物戒斷臨床研究的情況。研究人員在《精神病學時報》上撰文,就患者越來越多地使用在線論壇討論他們的藥物和退出藥物的情況向開藥者提供建議。研究人員建議,要收集的信息是醫生沒有準備好應對戒斷障礙。臨床醫生應向精神病學期刊尋求指導,以幫助“正確權衡使用苯二氮卓類藥物和抗抑鬱藥治療抑鬱症和焦慮症的風險和益處”。
最後,臨床醫生對戒斷信息的疏忽可能會因更系統性的失職而加劇。講述他們在荷蘭的經歷時,Groot 和 van Os發現,治療界的多方都對探索退出話題產生了抵制:
近年來,我們很難與我們的健康保險公司、荷蘭精神病學協會、全科醫生協會、患者保護組織 MIND、荷蘭國家醫療保健研究所甚至衛生部等相關方告知或討論這些問題的健康。在我們看來,當許多患者試圖討論他們的戒斷問題時,我們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經歷。理論、假設和對文獻的狹隘解釋才是最重要的。
製藥公司誤導處方者
比處方者缺乏關於戒斷的信息更令人不安的是製藥公司傳播有關它的錯誤信息。這尤其成問題,因為正如Cohen 和 Recalt解釋的那樣,“製藥行業通過直接或間接資助精神藥物的測試來主導精神藥物的測試,同時控製藥物信息的大多數分銷渠道。”
具體來說,製藥公司通過鼓勵他們將戒斷症狀解釋為複發的跡象——診斷出的精神健康狀況的症狀再次出現——而不是對停藥的反應,從而誤導了開藥者。正如傑克遜博士所觀察到的:
通過影響治療指南、期刊增刊、CME(繼續醫學教育)專題討論會和公告的內容和傳播,製藥公司推動了將戒斷症狀誤解為複發的證據,對此藥物治療的恢復得到了強烈支持.
此外,目睹他們被告知的是複發,精神科醫生(和患者)被鼓勵相信診斷出的疾病是慢性的,因此需要更長時間的藥物治療。對於抗抑鬱藥,傑克遜將這一結果描述為製藥公司的故意策略:
[T] 抗抑鬱藥戒斷症狀的存在已被製藥業用來構建慢性病的神話,這是基於患者在停藥時反復出現抑鬱(或躁狂)特徵的經驗。
傑克遜解釋說,鑑於抑鬱症的慢性性質,該行業為藥物療法提出了“預防效率”的論點,其中長期治療是預防復發的最佳手段。換言之,由於停止藥物治療會導致高複發率,因此應維持患者用藥以防止複發。
處方者因未能仔細觀察患者而成為該系統的同謀。處方者並沒有區分這些新的戒斷引起的症狀,而是將它們歸因於心理健康診斷本身。一些開藥者甚至在遇到奇怪的症狀時也會這樣做,例如腦震盪,這些症狀與所開藥物的疾病無關。這種將這些症狀歸因於復發的模式讓Framer感嘆:“你知道醫生一定不能聽他們的病人告訴他們什麼。”
通過這些方式,製藥公司隱藏了他們開出的藥物的戒斷作用,而處方者卻無法發現。正如傑克遜所譴責的那樣:“無論是出於無知還是有意為之,心理健康行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沒有意識到自己造成的這場悲劇。”
傑克遜 2005 年的不滿今天仍然成立。2019 年,研究人員Cohen 和 Recalt在涵蓋多種藥物類別的研究中分析了復發和戒斷的合併情況。他們在以預防復發為重點的臨床試驗中發現了普遍的“戒斷混雜”(戒斷症狀與復發證據的混淆),並警告說“估計這種混雜的真實程度還處於起步階段。”
這種混淆的部分原因是,儘管對複發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在過去的 30 年中,很少有原始試驗調查退出是否會表現為複發。” 然而,允許忽略退出的複發研究中的缺陷並非不可避免,作者提供了重新設計研究以降低退出混淆風險的藍圖。不幸的是,他們“對 [他們的] 廣泛建議很快就會採取行動並不樂觀。”
經濟激勵措施鼓勵開藥者維持患者服藥
開處方者也有經濟激勵措施來維持患者接受精神科藥物治療。報銷處方的開藥者在繼續服藥方面具有經濟利益,並且很少有動力花時間深入研究患者的痛苦。正如精神病學家史蒂夫·巴爾特所寫:
這也將有助於讓(如果不需要的話)有更多的時間與精神病患者相處。這個很重要。如果我只有 15 到 20 分鐘的時間和一個病人在一起,我就沒有時間詢問她持續的背痛、她闖入的姐夫或她的可卡因習慣。相反,我必須將我的問題限制在與我在上次就診時開具的藥物有關的問題上。當然,這為確認偏差創造了絕佳的機會——我看到了我期望看到的東西。
專注於藥物管理,而不是其他類型的治療反應可能解決的問題,成為常態。
製藥業也有很多錢,以至於它對精神病治療的影響是深遠的。討論 SSRI 所產生的美元,Will Self觀察到,“它可以扭曲整個職業的動力和道德規範。” 例如,開藥比進行治療更有利可圖。隨著精神科醫生轉向前者,他們的收入越來越與處方掛鉤。精神病學家丹尼爾·卡拉特(Daniel Carlat)在美國心理學會的心理學監測中被引用,他解釋說:
精神科醫生開處方而不是進行心理治療有巨大的經濟誘因…… 作為一名開藥者,你可以賺到比治療師多兩、三、四倍的錢。這裡的惡性循環是,由於精神科醫生將他們的實踐主要限制在開處方上,他們會因自然減員而失去治療技能,甚至更少進行治療。
金錢在精神病學中影響的一個更明顯的例子是製藥公司向臨床醫生提供現金支付給他們的產品的做法。最後,開藥者可能會認為不讓患者繼續服藥會帶來經濟風險;開藥者可能認為未服藥的患者病情惡化,導致復發、住院、無家可歸或暴力,可能會使臨床醫生受到經濟處罰或承擔責任。
這些經濟激勵措施可能會影響精神科醫生讓他們的病人繼續服藥。
對循證醫學的依賴使開處方者與患者的戒斷經歷隔離開來,而沒有提供承諾的好處
精神病學從 1990 年代開始接受循證實踐(又名循證醫學),這加強了開處方者與患者經歷的分離。傑克遜解釋說,臨床醫生曾經從患者的經驗中學習,她將這種方法稱為“基於現實的醫學”。她引用了大衛·希利的話,他在《精神藥理學的創造》中描述了“一旦精神藥理學文獻被賦予了臨床醫生的權威,他們直接知道他們在描述什麼。”
漸漸地,醫生開始更多地依賴循證醫學而不是直接觀察來進行教育。鑑於沒有其他匯總患者數據的來源,依賴此類試驗是有道理的。但是,雖然循證實踐的支持者吹捧隨機、安慰劑對照臨床試驗(RCT) 作為答案,但這些試驗並非沒有它們旨在克服的問題。
RCT 無法擺脫偏見是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2018 年對專業期刊中最常被引用的 RCT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由於各種原因,它們產生了有偏見的結果。原因包括:“參與者的影響結果的背景特徵通常在試驗組之間分佈不均,試驗經常忽略有助於其主要報告結果的替代因素,以及許多其他問題,試驗通常只是部分盲法或非盲法。 ”
儘管進行了多次控制,作者還是發現了偏見:
RCT 面臨著一系列強有力的假設、偏見和限制,這些假設、偏見和限制尚未在文獻中進行全面討論。本研究評估了全球被引用次數最多的 10 項 RCT,並表明試驗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偏倚。試驗涉及復雜的過程——從隨機化、盲法和控制,到實施治療、監測參與者等——需要在不同層次上做出許多決策和步驟,這些決策和步驟會帶來他們自己的假設和對結果的偏見程度。
在 2018 年對 RCT 的另一項分析中,研究人員還質疑將 RCT 作為無偏見證據來源的依賴。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許多此類試驗“沒有針對其他偏見來源設置盲法,也沒有充分控制,而且確實有很多不能這樣做,而且很少提供充分的辯護來保證公正性沒有受到破壞。” 他們認為,醫學界對 RCT 的巨大轉變以獲取有關精神科藥物的信息是不謹慎的:
取決於我們想要發現什麼、為什麼要發現它以及我們已經知道的,通常會有更好的調查途徑,對於 RCT 可以幫助的許多問題,還有大量其他工作——經驗、理論和概念——需要做以使 RCT 的結果可用。
研究人員自稱“不反對隨機對照試驗,只是對它們進行神奇的思考”,得出的這一結論應該重新提出傑克遜 2005 年關於精神藥理學研究依賴隨機對照試驗的警告。
而且,在 2020 年,兩組研究人員實際上已經將傑克遜的懷疑論應用於戒斷研究。Cohen 和 Recalt專門撰寫了關於戒斷研究的文章,提供了一份詳盡的藥理學 RCT 潛在偏見列表:“[N] 早期,每一種可能有利於測試藥物的策略都被納入了傳統的精神藥理學 RCT 的設計中。” 此外,隨機對照試驗通過發表或報告偏倚誇大了藥物的療效估計。
這些研究人員對最近重新評估 RCT 使用的步驟表示讚賞。Groot 和 van Os 也對 RCT 在戒斷研究中的使用提出了質疑。他們列舉了一系列問題,包括原始研究的數據有限(與研究評論相反)、對多藥治療缺乏關注,以及缺乏對弱勢患者群體的信息應用。
因此,傑克遜關於超越 RCT 來捕捉和解決個人用藥經驗的建議仍然很明確。她寫道,隨機對照試驗可能會提供一些信息來幫助進行分析,但它們並沒有消除評估手頭具體情況和考慮其他方法的需要。正如傑克遜所說,循證實踐的目標是掩蓋個體之間的差異,但考慮患者(和從業者)的個性對於康復至關重要。
目前對循證實踐的依賴導致臨床醫生更傾向於臨床試驗認可的治療方法,而不是未經臨床試驗認可的治療方法。傑克遜認為,這樣做會降低其他形式的知識——病人和醫生的價值觀、理論和直接觀察。
最新的戒斷研究反映了傑克遜對 RCT 未能捕捉個體患者體驗的擔憂。Cohen 和 Recalt認為,在 RCT 中患者聲音的減弱,以及缺乏解決問題的主動性,對於解決戒斷問題來說是一個壞兆頭。“雖然存在‘患者報告結果’的衡量標準,但它們尚未作為主要結果納入精神藥理學 RCT 中。”
Groot 和 van Os同意並走得更遠——不僅應該重視退出過程中的患者結果,而且還必須接受他們關於該過程的想法和冒險:“必須更加認真地對待患者的經驗、想法和倡議,即使這些信息沒有在科學文獻中發表,甚至當它們被認為包含‘關鍵’信息時也是如此。”
最後,我們目睹的從經驗經驗中獲取知識到從循證研究中學習知識的轉變造成了更大的損害。它削弱了處方者和患者之間的關係和反饋循環,這對於理解戒斷的影響是非常必要的。傑克遜在評論這些丟失的信息時直截了當地指出,“醫療信息的充分性值得懷疑。”
情境中的退縮經驗:對傳統精神病學的批判
精神科處方者必須了解戒斷,因為這些知識將為他們的整個專業實踐提供信息,並希望使處方者在考慮化學治療時更加謹慎。當他們這樣做時,處方者希望能夠認識到,戒斷故事不僅加強了對精神病學醫學模型的現有批評,而且首先提出了關於開具精神科藥物的優點的新問題。
在有據可查的文獻中,Grace E. Jackson、Stuart Kirk、Tomi Gomery 和 David Cohen、Peter Breggin和Robert Whitaker等人對使用精神科藥物治療心理健康問題提出了質疑。這些批評者對精神藥物治療的幾乎所有方面提出了質疑,包括診斷類別的創建及其使用、藥物的開發、測試和批准、此類藥物的處方和監測,以及對有效替代品缺乏關注。
對傳統精神病學的批判以簡化的形式寫道:
- 診斷類別是人類創造的,偽裝成生物科學。
- 藥物試驗通常由那些能夠從他們的成功中獲利的人進行。
- 這些試驗通常不跟踪超過一到三個月的療效。
- 一些試驗結果表明藥物比實際更有效。
- 成功的試驗會發表,而不成功的則不會。
- 製藥公司在壓制不利數據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
- 製藥公司向專業人士銷售此類藥物。
- 雖然精神活性藥物被宣傳為治療大腦“化學失衡”的方法,但這些失衡 無法確定。
- 在許多情況下,患者服用藥物的時間比最初預期的要長得多。
- 藥物可能並不比安慰劑更有效,而患者認為安慰劑效應可能帶來的好處。
- 心理治療可能比藥物治療更有效。
- 接受替代藥物治療的患者可能比接受替代藥物和藥物組合治療的患者做得更好。
- 社會支持和活動可能是促進康復的關鍵。
- 藥物可能會失去它們確實具有的任何功效,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損害一個人的心理健康。
- 藥物副作用可能很嚴重,並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惡化。
- 這些副作用,例如性功能障礙,可能會加劇心理健康問題。
活動家現在必須擴大這一改革論點,以涵蓋退出問題。關注以下錯誤將是一個起點:
- 處方者缺乏明確的指導方針來評估患者何時可以或應該停藥或幫助患者這樣做。
- 如果藥物的副作用發生在個別病例中,沒有規則可以確定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 大多數醫生不太可能向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FDA) 報告他們觀察到的不良反應,從而導致對藥物影響的了解不足。
- 由於缺乏指導和/或激勵,開藥者在沒有太多審查或理由的情況下連續數月和數年不恰當地維持患者用藥。
- 製藥公司鼓勵開藥者相信戒斷症狀是複發的跡象,並利用這一理論來鼓勵長期維持用藥。
- 許多患者花費數月和數年時間試圖戒除精神科藥物,有些人從未成功。
- 所有類型的精神科藥物都會在很大一部分患者中引起戒斷症狀,其中一些是嚴重且持久的,即使在停藥後也是如此。
- 除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例如,Paxil和苯二氮卓類藥物),FDA 很少介入並要求製藥公司警告退出精神科藥物的風險。
當在更廣泛的精神病學批評的背景下理解戒斷故事時,它們就會獲得額外的合法性。開處方者需要承認並從這些經驗中學習變得更加清晰。開處方者可以通過查看在線社區的世界來開始這個過程,這些社區填補了傳統精神病學留下的空白。
在本系列的第 2 部分中,我們將介紹在線社區及其提供的服務。
***
Mad in America 擁有不同作家群體的博客。這些帖子旨在作為一個公共論壇,廣泛地討論精神病學及其治療。所表達的意見是作者自己的。

詹妮弗·霍尼格Jennifer Honig 是心理健康法律顧問委員會的高級律師,該委員會是馬薩諸塞州最高司法法院的一個機構,旨在為有心理健康問題的貧困人士提供支持。自 1992 年以來,她一直從事精神衛生法領域的工作。
Jennifer HonigJennifer Honig is a Senior Attorney at the Mental Health Legal Advisors Committee, an agency of the Supreme Judicial Court of Massachusetts that advocates for indigent persons with mental health issues. She has practiced in the area of mental health law since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