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HD:一場具有破壞性的精神醫學騙局
作者:Philip Hickey, PhD – 2016年10月30日
引言
今年早些時候,紐約時報的調查記者艾倫·施瓦茲(Alan Schwarz)出版了他的最新著作《ADHD Nation》(ADHD國度)。
書籍封面上的介紹寫道:
「超過七分之一的美國兒童被診斷為ADHD——這是專家所認為合理比例的三倍——這意味著數百萬的孩子被誤診,並服用像Adderall或Concerta這樣的藥物來治療他們可能並沒有的精神疾病。每年這個數字都在增加。然而,許多專家和藥廠仍然否認有任何值得擔憂的原因。事實上,他們還聲稱,成年人和全世界應該接受ADHD,而這些藥物將改變他們的生活。
在《ADHD Nation》中,艾倫·施瓦茲審視了這一文化和醫學現象的根源及崛起:ADHD的奠基人基思·康納斯醫生(Dr. Keith Conners)花了五十年時間提倡像利他林(Ritalin)這樣的藥物,直到他意識到自己參與了如今被他稱為‘具有危險規模的國家災難’;一個陷入困境的年輕女孩和一個勤奮的青少年男孩被捲入了不斷擴大的ADHD機器,服用了效果極差的藥物;而大藥廠(Big Pharma)則過度宣傳這種疾病,並從錯誤處理孩子(現在也包括成年人)中賺取了數十億美元。」
這些說法幾乎無人能反駁。然而,介紹接著寫道:
「在證明ADHD是真實存在的,且在適當的情況下可以用藥物治療的同時,施瓦茲發出了早該響起的警鐘,並敦促美國解決這日益嚴重的國家健康危機。」
當然,這正是我們分歧的地方。
當我第一次讀到書封上的介紹時,我很好奇艾倫·施瓦茲(Alan Schwarz)會使用哪些論據來支持ADHD是「真實的」這一主張,以及它有時需要「藥物治療」的說法。讓我們先明確「真實」這個詞的含義。沒有人否認注意力不集中、過度活躍和衝動行為可以是現實問題。然而,爭議的核心在於,是否有意義將這些模糊定義的問題視作一種疾病。通常,當人們說或寫ADHD是「真實的」,他們的意思是,這些被美國精神醫學協會(APA)的診斷和統計手冊(DSM)列出的問題群是一種真實的、經得起檢驗的疾病——就像糖尿病一樣;而「患有」這種所謂疾病的人必須像糖尿病患者需要胰島素一樣服用「藥物」。因此,書封上所說的施瓦茲將證明ADHD是一種真實疾病,顯得意義重大。正如我之前所說,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他是否在這場辯論中能提出任何新的觀點。
這是書中序言的開頭頁面:
「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是真實存在的。不要讓任何人告訴你相反的說法。
一個在家中和繁忙街道上瘋狂亂竄的男孩,可能會危及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一個連兩分鐘都無法安靜坐著聽課的女孩,將無法學習。一個無法集中注意力準確填寫健康保險表格的成年人,無法應對現代生活的要求。當一個人在任何年齡段經歷這些困難的組合——嚴重到影響其日常生活功能——且沒有其他合理的解釋時,那麼他很可能患有一種嚴重的,但仍有些神秘的病症,醫學界稱之為ADHD。
沒有人完全知道這種病症的成因。最常見的理論是,經典ADHD的過度活躍、注意力缺乏和衝動行為是由大腦中的化學物質和突觸之間的某種功能失調引起的。一個人的環境顯然也扮演著角色:混亂的家庭、不靈活的課堂或令人分心的工作場所,都可能誘發或加重症狀。不幸的是,像許多精神疾病一樣,例如抑鬱症或焦慮症,ADHD目前沒有確定的診斷方法,沒有血液檢測或CT掃描能讓醫生宣告:‘好,這就是了’——能做的只有謹慎評估行為的嚴重程度是否足以構成診斷。(畢竟,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心或衝動行為。)但有一點是確定的:ADHD沒有治癒方法。患有這種疾病的人或許能學會適應,可能在藥物的幫助下,但無論年輕還是年老,患者通常被告知他們將終身與自己異常的大腦共處。」(第1頁)
這就是問題所在。我們來仔細看看。
「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是真實的。不要讓任何人告訴你相反的說法。」
「ADHD」的真實性與否是整場辯論的核心問題,從這個開場聲明中很明顯,施瓦茲並沒有以一個調查記者應有的開放心態來探討這個問題。
但情況變得更糟。
「一個在家中和繁忙街道上瘋狂亂竄的男孩,可能會危及自己和他人。」
施瓦茲先生顯然試圖創造一種印象,認為這種行為對於「患有ADHD」的兒童是相當典型的,他也指出這些行為是嚴重的。然而,他沒有提到,或許甚至沒有意識到,身體上危險的活動——包括「不看路就跑進街道」——曾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修訂版(DSM-III-R)中ADHD的具體標準之一,但在《DSM-IV》中被淡化為「在不適當的情況下經常跑來跑去或爬高爬低」。而在《DSM-5》中,「過度地(excessively)」這個詞被刪除了。以下是這三個版本中的實際條目:
DSM-III-R(1987年):
「(14)經常從事身體上危險的活動,而不考慮可能的後果(非為了追求刺激),例如:不看路就跑進街道」(第53頁)
DSM-IV(1994年):
在「過度活躍(Hyperactivity)」小節下:
「(c)在不適當的情況下經常跑來跑去或爬高爬低(在青少年或成人中,可能僅限於主觀的坐立不安感)」(第84頁)
DSM-5(2013年):
在「過度活躍和衝動性(Hyperactivity and impulsivity)」小節下:
「c. 在不適當的情況下經常跑來跑去或爬高爬低。(註:在青少年或成人中,可能僅限於感到坐立不安。)」(第60頁)
因此,一個在家中和繁忙街道上瘋狂亂竄的男孩,可能在這三個版本中都符合標準,但——這是關鍵點——在後來的版本中,並不需要此類極端行為就能被計為一個「症狀」。與施瓦茲先生暗示的說法相反,一個孩子並不需要表現出如此極端或危險的行為,就能符合美國精神醫學協會(APA)對這種所謂疾病的任何標準。而且特別需要注意的是,自1994年以來,對於成人和青少年,在這一項中唯一的要求是他們感到坐立不安!
. . . . . . . . . . . . . . . .
「一個女孩甚至無法靜坐兩分鐘聽老師講課,她將無法學習。」
艾倫·施瓦茲,或其他任何人,如何能夠推斷出一個不注意聽老師講課的女孩,無法專注?這是一個無效的推論,但在精神醫學中卻是標準操作。
. . . . . . . . . . . . . . . .
「當一個人在任何年齡段經歷這些困難的組合——嚴重到影響其日常功能——且沒有其他合理的解釋時,那麼他很可能患有一種嚴重的,雖然仍有些神秘的病症,醫學界稱之為ADHD。」
這又是精神醫學中的標準說辭:問題出在「……沒有其他合理的解釋……」這一短語中。
任何曾經有過哪怕一點點與孩子和家庭工作經驗的人都可以證明,如果有心尋找,總會有其他的心理社會因素可以解釋這些問題。然而,現實情況是,在精神醫學的實踐中,這些替代解釋幾乎從不被尋求。
而不尋求的原因是,精神醫學有效地關閉了這類思考的門。在精神醫學的框架內,如果一個孩子(或成年人)符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中列出的任意且本質上模糊的標準,那麼他就被認為患有一種叫做ADHD的腦部疾病。因此,尋找心理社會解釋的概念不僅從未發生,而且在精神醫學中甚至會被視為荒謬。
在真正的醫學中,如果一個人患有肺炎,那麼這就是他持續咳嗽、痰液黏稠、虛弱等症狀的解釋。此時,醫生在這種情況下尋找替代的心理社會解釋是毫無意義的。同樣地,精神科醫生牢牢依賴他們錯誤的疾病觀點,不會尋找對所遇問題的普通人類解釋。當然,精神醫學與真正醫學的區別在於,後者的診斷確實是對症狀的真實解釋。而在精神醫學中,這些「診斷」僅僅是精神科醫生為模糊的問題群體貼上的標籤,並不具備任何解釋價值。
為了說明這一點,請考慮以下兩個假設的對話。
客戶家長:為什麼我兒子這麼容易分心?為什麼他在學校作業中犯這麼多錯誤?為什麼我跟他說話時他不聽?為什麼他這麼沒條理?
精神科醫生:因為他患有一種叫做注意力缺陷/過度活躍症(ADHD)的疾病。
家長:你怎麼知道他有這種病?
精神科醫生:因為他很容易分心,學校作業中犯了很多錯誤,當你跟他說話時他不聽,而且他非常沒條理。
關鍵在於,在精神醫學中,對「疾病」的唯一證據就是它試圖解釋的行為本身。換句話說:你的兒子分心,是因為他分心。
將此與真實醫學中的類似對話進行對比。
病人:為什麼我這麼疲倦?為什麼我的體溫突然飆升?為什麼我吐出的痰這麼可怕?
醫生:因為你患有肺炎。
病人:你怎麼知道我得了肺炎?
醫生:因為我能聽到聽診器中具有特徵性的聲音;你的胸部X光顯示雙肺中有大量積液;你的痰液實驗室檢測結果顯示有肺炎球菌;而且你告訴我的所有症狀都與這個診斷相符。如果你想看,我可以給你看X光片。
在這段對話中,推理中沒有循環邏輯。肺炎是症狀的原因,並構成了一個真實且有用的解釋。
. . . . . . . . . . . . . . . .
「‘沒有人完全知道它的成因。’」
事實上,很多人都知道孩子為什麼會在家中和繁忙街道上瘋狂亂竄。原因很簡單,就是他們在適當的年齡沒有被灌輸足夠的紀律和自制力來抑制這種行為。而這並不是「有點神秘」。這是自史前時代以來,父母和祖父母一直在處理的事情。同樣,其他被誤導地稱為《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中的「症狀」的ADHD行為也適用這個道理。
. . . . . . . . . . . . . . . .
「‘最常見的理論是,經典ADHD的過度活躍、注意力不足和衝動行為,源於大腦中化學物質和突觸之間的某種功能失調。’」
就在我們以為那個早已失去信譽的化學失衡騙局要結束的時候!施瓦茲先生似乎沒有意識到,目前大多數主要的精神科醫生正忙著與這種荒謬理論保持距離,這理論曾在數十年內支撐了精神醫學的騙局。非常著名且極具威望的塔夫茨大學精神科醫生羅納德·皮斯醫生(Ronald Pies, MD)甚至斷言,精神醫學從未推廣這種騙局——這一說法為學術界的象牙塔增添了全新的寓言維度。
接著施瓦茲先生切入主題:
「‘不幸的是,與許多精神疾病一樣,例如抑鬱症或焦慮症,ADHD沒有確定的診斷方法,沒有血液檢測或CT掃描能讓醫生宣告,‘好,就是這個’——所能做的只是仔細評估行為的嚴重程度是否足以構成診斷。(畢竟,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心或衝動行為。)’」
儘管之前的說法模糊不清,並且儘管施瓦茲先生譴責了他所描述的ADHD過度診斷現象,但他顯然仍然堅定支持精神醫學的主張:如果注意力不集中、衝動和過度活躍行為達到某種未明確定義的嚴重性門檻,這些行為就構成了一種疾病。
這是精神醫學的另一個核心謬誤,經常被推廣,不僅在連續出版的DSM(《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版本中,還包括精神醫學界最有名望的支持者的辯護文章中:如果一個人在思維、情感或行為上出現的問題超過某種任意且模糊的嚴重性、持續時間或頻率門檻,通過某種只有精神醫學理解的「煉金術」,這些問題便會變成一種疾病。儘管從未發現任何有機病變,這一事實在此毫無意義。如果問題足夠嚴重,那麼它就是一種疾病。
而造成這種荒謬的原因是,在精神診斷的鏡像世界中,問題的原因並不重要。這正是羅伯特·斯皮策(Robert Spitzer)在其DSM-III及後續版本中體現的現象學方法的關鍵點。為什麼一個人表現出這樣的問題並不重要。比如說,當一個孩子表現出ADHD的症狀,即便文本中對其定義鬆散,只要他達到注意力不集中、過度活躍和衝動的程度,那麼他就被認為患有這種疾病。無論這些行為是由於鬆散的管教、不一致的教育、溺愛的教養、手足競爭、情感虐待,還是其他原因導致,對於「診斷」來說都沒有影響。
這與真正的醫學形成了鮮明對比。在真正的醫學中,診斷與病因幾乎是同義的;而在精神診斷中,問題的原因無關緊要。如果孩子表現出這些行為,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或病因,那麼他就「患有這種疾病」。事實上,這種「疾病」僅僅是模糊定義的問題行為的存在而已。並不需要證實有神經病理學上的異常,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些行為涉及神經病理學上的問題。《DSM-III》將這種方法描述為「……對病因學或病理生理過程保持非理論性的態度,除非對某些疾病已經得到充分確立並因此納入其定義之中」(第23頁),但這不適用於ADHD。
《DSM-III-R》非但沒有承認這種「非理論性」方法的明顯不誠實,反而將其視為一種優點:
「在《DSM-III》和《DSM-III-R》中,採取非理論性方法處理病因的主要理由是,將病因理論納入手冊將成為使用者的障礙,因為對每一種疾病來說,無法呈現所有合理的病因理論。」(第23頁)
然而,實際情況是,通過忽視病因學問題,美國精神醫學協會(APA)創造了一種語境,在這種語境下,任何人類問題都可以隨意被定義為「精神障礙」,而這些「障礙」可以且實際上確實迅速轉變為「精神疾病」,正如我們在施瓦茲先生的文字中看到的,這些疾病被與神經化學失衡掛鉤。精神醫學輕鬆地拋棄了「新診斷必須基於經證實的有機病理學」這一理念。真正的醫生通過艱苦的研究和學習來發現新的疾病——這往往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時間。而精神醫學則僅憑想像創造出這些疾病,並通過委員會投票確認其本體論上的有效性。
數十年來,精神醫學,依仗著知道很少有人會閱讀《DSM》,在有機病理學缺失這一問題上公然撒謊。他們對客戶、公眾和媒體謊稱「化學失衡」的存在並且是問題的根源。而且——這是最大的謊言——這些藥物可以糾正這些並不存在的失衡。他們還經常聲稱,他們的「病人」在許多(甚至大多數)情況下,可能需要終生服用這些藥物。在這一點上,施瓦茲先生也完全追隨了他的精神醫學導師們的步伐。
「有一件事是確定的:ADHD無法治癒。」
再次注意這種教條式的傲慢。那些注意力不集中、行為不端、無法聽從命令、在DSM中被模糊定義的程度上造成破壞的孩子,被認為無法獲得適齡的紀律!施瓦茲先生怎麼可能知道這一點呢?早在1973年,胡西(Huessy)、馬歇爾(Marshall)和詹德隆(Gendron)的研究(從二年級到五年級追蹤500名兒童的行為障礙患病率,《兒童精神病學報》(Acta Paedopsychiatrica),39(11), 301-309)就顯示出過度活躍行為並不是隨時間穩定的模式。還有大量從1960年代起的研究明確證明,即使是那些習慣性注意力不集中、衝動且過度活躍的兒童,也能夠通過訓練改變成更具生產力且不具破壞性的行為。事實上,在1960年代中期之前,這類研究根本不需要,因為父母和老師通常都能成功地訓練孩子控制自己的行為,專注於學習和家務。的確,父母和老師當時認為這是他們職責的一部分。然而,1968年,隨著《DSM-II》的出版,精神醫學的「頂尖專家」宣佈,這些問題行為構成了一種需要專家關注的疾病。這種「疾病」被稱為兒童多動反應(hyperkinetic reaction of childhood)。其描述只有四行:
「308.0 兒童(或青少年)多動反應*
這種障礙以過度活躍、坐立不安、注意力分散和注意力持續時間短為特徵,特別是在幼兒中;這種行為通常在青春期有所減輕。」(第50頁)
. . . . . . . . . . . . . . . .
「……無論年輕或年老,患者通常被告知他們將終其一生與自己異常的大腦共處。」
儘管數十年來有著巨額資金支持和強烈動機的研究,儘管有許多熱情洋溢、隨後被駁斥的相反主張,仍然沒有任何一絲證據表明那些被貼上ADHD標籤的人有任何腦部病理問題。事實上,沒有一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的版本,包括現行的《DSM-5》,曾將任何形式的腦部病變列為這種所謂疾病的診斷標準項目。《DSM-5》確實將ADHD歸類於神經發展障礙(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一節中,但這只意味著問題的發生時間在發展期。這並不需要有神經病理學上的依據。「神經發展障礙是一組在發展期發病的狀況。這些障礙通常在發展的早期表現出來,通常在孩子上小學之前,並且以導致個人、社會、學業或職業功能受損的發展缺陷為特徵。」(第31頁)將ADHD描述為一種神經發展障礙,對我而言,顯得極其具有誤導性,因為大多數人會將「神經發展障礙」這個術語解釋為涉及某種神經病變。美國精神醫學協會(APA)在此所做的是傳達了ADHD涉及神經病變的印象,卻無需提供證據證明這種情況的存在。
ADHD的「過度診斷」
接著施瓦茲先生進入他書中的主題:ADHD正被嚴重地過度診斷。這個主題也正是近年來許多精神科醫生採納的觀點,試圖挽救他們因反精神醫學批評而岌岌可危的行業。看看施瓦茲先生是如何處理這一點的:
「美國精神醫學協會(APA)對ADHD的官方描述,由該領域的頂尖專家編纂,用以指導全國醫生的診療,表明該病症影響約5%的兒童,主要是男孩。大多數專家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基準。
但現實中的美國情況如何?
美國15%的青少年——這是共識估計的三倍——被診斷為ADHD。這意味著數百萬額外的孩子被告知他們的大腦出了問題,其中大多數隨後服用了嚴重的藥物。全國男孩的ADHD診斷率達到了驚人的20%。在南方的一些州,如密西西比州、南卡羅來納州和阿肯色州,ADHD診斷率達到所有男孩中的30%,幾乎每三個男孩就有一個。 (男孩通常比女孩更活躍和衝動,女孩的ADHD更多表現為無法集中注意力。)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些縣,接近一半——一半——三到五年級的男孩正在服用ADHD藥物。
ADHD已經成為美國醫學中診斷最錯誤的病症,遠超其他。
然而,令人擔憂的是,蓬勃發展的ADHD產業鏈中,很少有人承認這一現實。許多人是出於善意——他們看到孩子在客廳、教室或候診室中掙扎,認為診斷和藥物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另一些人的動機更為混合:有時老師更喜歡少一些麻煩的學生,家長想要一個安靜的家庭,醫生也喜歡穩定的簡單業務。在最陰險的角落,則是被藥廠收買的知名醫生和研究人員,他們從ADHD無節制和不負責任的推進中賺取了數十億美元。」(第2-3頁)
但施瓦茲先生沒有提到,也可能根本不知道的是,那些為《DSM-5》制定ADHD標準的「頂尖專家」中,有69%是接受藥廠資助的,而施瓦茲先生隱含接受了這些專家的盛行率估計。
施瓦茲先生似乎也沒有意識到,這些制定ADHD標準的「頂尖專家」逐漸放寬了這種所謂疾病的標準。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列出了《DSM-IV》(1994年)中的放寬條件。《DSM-5》(2013年)的放寬標準包括:
– 對於青少年和成人,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狀」數量從6個減少到5個(第59頁)
– 對於青少年和成人,過度活躍/衝動的「症狀」數量也從6個減少到5個(第60頁)
– 《DSM-IV》規定,ADHD的某些症狀必須在7歲之前出現(第84頁)。《DSM-5》將這一發病年齡標準放寬至12歲(第60頁)。
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放寬條件既不是基於,事實上也不可能基於任何實證證據或科學研究。除了《DSM》連續修訂中的定義外,ADHD根本沒有其他定義。認為那些接受藥廠資助的「頂尖專家」能夠比較真實的ADHD與《DSM》中的描述,並發現不一致之處,這種想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實上,並沒有一個所謂的「真實的ADHD」。唯一的定義是美國精神醫學協會(APA)編造出來的,他們可以,而且確實在隨意更改這個定義。而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的變更都是朝著放寬標準的方向進行的。
. . . . . . . . . . . . . . . .
這才是核心問題。哀嘆ADHD的過度診斷是一種空洞且徒勞的行為,因為事實是:
– 標準極其模糊且主觀,
– 藥廠的利益隨著診斷範圍的擴大而增加,
– 精神醫學通過各種途徑分享這些利潤,
– 藥物具有成癮性,
– 學校因每名ADHD孩子的註冊而獲得額外資金,
因此,「診斷擴張」(”diagnosis creep”)是不可避免的。這不是某種意外或藥廠對精神醫學的蓄意破壞,儘管精神醫學一直試圖保持純潔和不受污染。「診斷擴張」是精神醫學有意且刻意創造的怪物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它是精神醫學擴張議程的一部分,並得到了羅伯特·斯皮策(Robert Spitzer)在《DSM-III》(1980)中所採取的非理論性、現象學方法的巨大助力。順便說一下,在ADHD的案例中,這種擴張在1980年之前就已經開始。這裡是Ullmann和Krasner在他們的《異常行為的心理學方法》(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Abnormal Behavior),第二版(1975年)中的一段話:
「那些被貼上‘多動’標籤的孩子的治療,在心理學和兒科領域引發了更多的爭議……藥物治療,特別是像安非他命這樣的興奮劑,已經成為流行的治療方式,甚至在某些學區中多達10%的學生都在服用這些藥物……」(第496頁)
即使在那時,41年前,已有明確的反對聲音:
「這個標籤加上藥物治療將孩子歸入心理疾病或生病的範疇,隨之而來的還有社會和自我標籤……藥物的使用增強了對外部因素有效性的信念,而不是將改變歸因於自己的努力(這在孩子自我控制能力和教師責任感的發展中是重要的一部分)」(同書,第497頁)
還需指出的是,標準的放寬並不限於ADHD。《DSM-5》還放寬了APA對精神障礙的定義,實際上擴大了所有所謂診斷的範圍。
《DSM-IV》(1994年)對精神障礙的定義是:
「……精神障礙是一種臨床上顯著的行為或心理綜合症或模式,會給個體帶來當前的痛苦(例如,痛苦的症狀)或障礙(即在一個或多個重要功能領域中的功能受損),或顯著增加個體遭受死亡、疼痛、障礙或重要自由喪失的風險。此外,這種綜合症或模式不能僅僅是對特定事件的預期反應或文化允許的反應,例如親人死亡。無論其原始原因是什麼,目前必須被認為是個體行為、心理或生物功能障礙的表現。除非偏差行為(例如,政治、宗教或性行為)或主要源於個體與社會的衝突是上述個體功能障礙的症狀,否則它們不屬於精神障礙。」(第xxi-xxii頁)
這一定義可以準確地概括為:任何在思維、情感和/或行為方面的顯著問題。事實上,極難想像在思維、情感和/或行為方面存在的顯著問題不在《DSM》內列出。
《DSM-5》(2013年)中的精神障礙定義與上述定義類似,但包含了更多的措辭,以及一個巨大的放寬。為了讓讀者自行判斷,以下是《DSM-5》的定義:
「精神障礙是一種以個體的認知、情緒調節或行為中的臨床顯著擾亂為特徵的綜合症,反映了心理、生物或發育過程中的功能障礙。精神障礙通常與社會、職業或其他重要活動中的顯著痛苦或障礙相關。對於常見壓力源或喪失的可預期或文化認可的反應,例如親人去世,不被視為精神障礙。社會偏差行為(例如,政治、宗教或性行為)和主要源於個體與社會的衝突不屬於精神障礙,除非這些偏差或衝突是個體功能障礙的結果,如上所述。」(第20頁)【強調部分】
第四行中的「通常」一詞大大擴展了精神病學「診斷」的潛在範圍。可以說,它變得如此寬泛,以至於可以涵蓋整個人口。關鍵在於,在《DSM-IV》中,問題必須達到某種顯著性或嚴重性程度。但在《DSM-5》中,這一要求實際上被放寬了。儘管兩者的措辭都很模糊,但《DSM-IV》要求痛苦或障礙的存在,顯然比《DSM-5》中所說的痛苦或障礙「通常」存在要更加嚴格。實際上,嚴重性門檻已被廢除,這清楚地邀請從業者將「診斷」賦予那些症狀較輕的個體。而且需要強調的是,這一變更並不是基於任何科學信息或發現。這一變更僅僅是APA的決定,旨在將他們所謂疾病的範圍擴展到幾乎全球所有人身上。
還需強調的是,這並非無足輕重的問題,因為這種變更已經在ADHD的案例中得到實施。比較《DSM-IV》與《DSM-5》中ADHD的嚴重性標準:
DSM-IV:
「D. 必須有明顯證據表明在社會、學業或職業功能方面存在臨床顯著的障礙。」(第84頁)【強調部分】DSM-5:
「D. 有明確證據表明這些症狀干擾或降低了社會、學業或職業功能的質量。」(第60頁)
再次強調,兩者的措辭都很模糊,但「臨床顯著的障礙」顯然是一個比「干擾或降低功能質量」更為嚴格的標準。
綜合這些考量,很難避免得出這樣的結論:APA不僅支持這種所謂診斷的廣泛擴展,而且數十年來一直積極推動並促成這一擴展。
. . . . . . . . . . . . . . . .
結論
施瓦茲先生很好地揭露了製藥公司(Pharma)的策略和手段。儘管這個故事大部分已為人熟知,並且以前也被講述過,他仍然將這個騙局呈現得詳細且易讀。他還探討了家長推動為孩子進行「診斷」並服用藥物的問題,以及人們確實會對這些藥物上癮的無可否認的事實。他也揭示了CHADD(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兒童與成人協會)與製藥公司之間的聯繫。
或許現在他可以看看更大的騙局:精神醫學將幾乎每一個有關思維、情感和/或行為的問題,包括兒童的注意力不集中、衝動行為和缺乏紀律,進行虛假的、破壞性的醫學化處理。
製藥公司確實使用非常值得質疑的方法來推銷他們的產品。但如果沒有精神醫學虛假且自私的「診斷」,他們不可能賣出任何一張利他林(methylphenidate)或其他精神藥物的處方。而且,沒有精神醫學提供的「診斷」標準放寬,他們也不可能將銷售額提高到如今的規模。批評匆忙完成的簡單檢查表是空談,除非人們也願意將批評指向《DSM》中同樣簡單的「症狀列表」,那些檢查表僅僅是它們的鏡像。
精神醫學只不過是合法化的藥物推銷。它所謂的分類體系沒有一絲智力或科學上的有效性。他們創造這些所謂的疾病來擴大他們的地盤,然後放寬標準以進一步擴展。
在醫療護理的幌子下,他們經常剝奪人們的能力感、尊嚴,並且在許多情況下剝奪了他們的生命。他們徹底破壞了「通過紀律性努力獲得成功」的概念,並將數百萬人困在他們不斷擴張的藥物依賴和自我懷疑的網中。他們並非施瓦茲先生所說的那些真正疾病的深思熟慮的專業編纂者。相反,他們是推銷藥物的騙子,系統性且故意地欺騙他們的客戶和公眾,以提高他們的聲望和收入。
如果有一個議題值得徹底的調查報導,那麼非精神醫學莫屬。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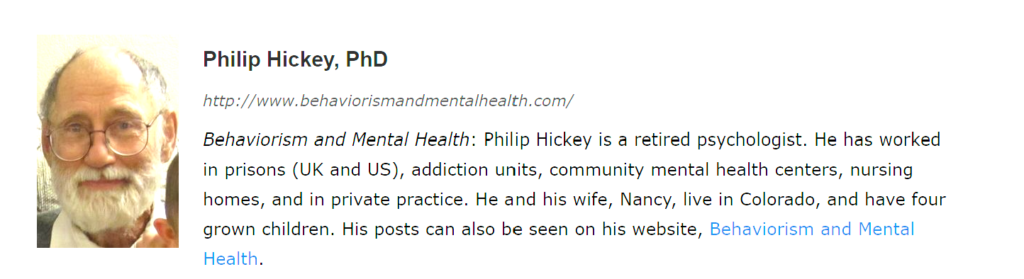
行為主義與心理健康網站:菲利普·希基是一位退休的心理學家,曾在英國和美國的監獄、戒癮機構、社區心理健康中心、療養院以及私人診所工作。他和妻子南希 (Nancy) 住在科羅拉多州,有四個已成年的孩子。他的文章也可以在他的網站「行為主義與心理健康」上找到。
MADTAIWAN備註
1.文章中的艾倫·施瓦茲(Alan Schwarz)是一位紐約時報的調查記者。他因其對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以及與此相關的藥物濫用問題進行深入調查而聞名。施瓦茲的著作《ADHD Nation》(《ADHD國度》)探討了ADHD在美國文化和醫學領域的興起,特別是其診斷率過高以及藥物過度使用的問題。書中他批判了藥廠、醫學界和其他推動ADHD藥物的人士,並且強調了許多孩子和成人可能因為被誤診為ADHD而服用了不必要的藥物。施瓦茲同時也認為ADHD是存在的,但強調應該謹慎使用藥物治療。
2.診斷與統計手冊:精神病學最要命的騙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