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場致命的流行病:成人ADHD和刺激藥物? 作者:Mark Ragins醫生 – 2018年5月20日
我有時會想,如果我是當初在大力推廣使用鴉片類藥物時開始自由處方的醫生,如今因這導致了致命的流行病,我會感到多麼內疚。這不只是隨意的思考。我現在正被敦促去推廣我擔心可能成為下一場致命流行病的東西——刺激藥物。我是一名大學精神科醫生,可以說正處於這場新興的ADHD/刺激藥物危機的「零地點」。這週我受到了巨大的壓力……我感到非常憤怒。
我參加了在紐約舉行的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年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15,000名精神科醫生一同參加。一場名為《成人ADHD:基於證據的藥物治療算法》的會議擠滿了數百名與會者,由哈佛的David Osser、Robert Patterson和Bushra Awidi醫生主講。我們正在尋求有見地的指導,因為我們面對越來越多的患者,這些患者在得知自己有ADHD後,正在尋求使用刺激藥物來應對這種情況。我們得到了一個比預期更簡單的答案:給他們全部開高劑量的刺激藥物,通常甚至超過FDA推薦的劑量。如果他們有雙相情感障礙、物質濫用、酗酒或濫用刺激藥物,可能需要謹慎一些,但總的來說,儘管如此,還是可以給他們開刺激藥物。
真的嗎?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聯繫他們,或者查閱他們即將在 psychopharm.mobi 上發布的ADHD算法。
他們怎麼能得出如此顯然不負責任的建議?
因為這是「基於證據」的隨機對照研究。我要指出的是,幾乎所有的隨機對照研究都是藥物研究,因此他們只能根據「證據」來推薦藥物。這些研究要麼是為了獲得FDA批准新藥或新適應症的短期研究,要麼是直接或間接由製藥公司及其盟友資助的研究,目的是為了廣告宣傳。並沒有任何嚴肅的長期研究,無論是藥物的效果還是其危險性,也沒有研究如何停止使用這些藥物。
在這些「數據的限制」範圍內,研究顯示新型刺激藥物在短期內非常有效,並且相對安全。除了Strattera之外,沒有其他治療方法——包括像Wellbutrin或clonidine這類的舊專利藥物,或者應對技巧和適應措施——被研究過,因此它們不被納入這個算法。
因此,我們現代的科學方法論的盲點,不管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最終導致了這些短視的處方習慣,在我看來,這種情況是常見的。
那麼,你打算怎麼做?
簡短的回答是:在有人能告訴我如果一個新生開始每天服用刺激藥物,他們在畢業前失控並最終變得精神錯亂的機率是多少之前,我不會給任何學生開刺激藥物。我知道這個機率不是零,因為我見過發生這樣情況的人,但我不知道這到底有多少。有人請在某所大學進行這樣的研究——之後我們可以討論多少是「可接受的風險」。順便說一句,我認為大多數學生「濫用」刺激藥物的方式——即只有在他們拖延到落後或需要參加難考試時才服用——可能比每天按照這些哈佛醫生推薦的高劑量服用「使用」它們要安全。
長答案:ADHD(或更準確地說是ADD),比大多數DSM-5診斷更容易將有注意力問題並「符合標準」的人與那些實際上患有基礎精神疾病的人混為一談。當他們說80%的ADHD患者有其他共病(我不知道這個數據來自什麼人群或方法),對我來說,這意味著絕大多數時候,診斷為ADHD的人其實是因為其他狀況干擾了他們的注意力,而不是ADHD。如果我們加上創傷——例如「發展性創傷障礙」、童年性虐待和強姦受害者,這些情況非常常見,但不在DSM-5中——誤診(在我看來是誤治)的人的數量會更高。許多負責任的臨床醫生會在做出ADHD診斷並開具刺激藥物之前,仔細了解患者的童年史,甚至收集相關記錄,以查找注意力問題的潛在且通常可治療的原因,即使DSM-5不要求這樣做。
對於那些沒有其他潛在因素干擾他們注意力的人(例如最近的分手),我們可以將他們的問題「正常化」,認為這是他們的注意力跨度與生活中所需注意力不匹配的結果。我們每個人的注意力跨度都有一定範圍——而這個範圍正在逐漸縮短,這讓越來越多的人出現問題,因此也變得「可診斷」。如果回顧過去100年,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從聽收音機並跟隨棒球這種節奏緩慢的國家運動的世代開始的進程,接下來是我的世代,我們從小訓練大腦觀看電視和《芝麻街》的短篇節目,並習慣於美式足球的節奏,而現在,我們正在被一個在電子遊戲、上網和iPhone中成長的世代取代,對於這個世代來說,連籃球的刺激性都不夠了。
儘管我們已經能夠改變體育、娛樂和音樂的節奏來適應我們越來越短的注意力跨度,但我們並沒有真正從根本上改變學校的節奏,這就是大多數人困難的地方。此外,注意力跨度縮短使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變得更加困難——包括與自然建立聯繫、足夠關注我們的浪漫伴侶和其他人際關係以便分享我們的生活、充分關注我們的孩子以便給予他們發展所需的「鏡像反應」,以及花時間通過集體或個人祈禱與上帝建立聯繫。
當我遇到一個人的注意力一直處於注意力範圍的低端,且沒有其他可治療的原因時,即使他們能進入大學,但仍因這些問題感到痛苦,我會向他們提供:1)應對技巧、適應和便利措施(通常通過殘疾學生辦公室),2)試用Wellbutrin(雖然效果不如刺激藥物,但危險性也小得多,且不具成癮性),3)一個長期且艱難的訓練計劃,旨在重新訓練他們的大腦以更好地專注,通常被稱為冥想(我告訴他們,當我開始冥想時,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才能在不分心的情況下數到10次呼吸)。
我還告訴他們,儘管刺激藥物幾乎可以幫助每個人提高專注力,但我過於謹慎,不願意因為開具刺激藥物而危害他們的大腦和生活。
我拒絕成為那些促成下一場致命流行病的醫生之一。如果你認為我過於謹慎,我希望你是對的,但我看到了太多刺激藥物和鴉片類藥物之間的相似之處。它們都強烈誘發心理和身體的依賴,刺激我們的愉悅中心,通常被正常人「濫用」(我們試圖製造出不易濫用的配方,而街頭販子則製造出更強、更易濫用且更危險的配方),即使是在處方劑量下,長期使用也會對精神和身體產生危險影響。或許最重要的是,它們在短期內「有效」,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解決任何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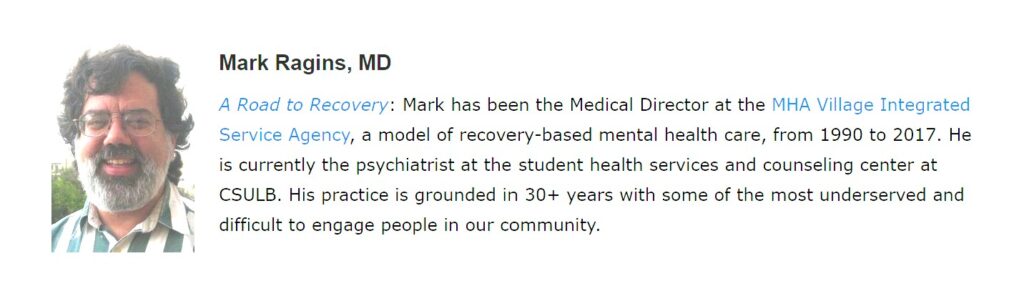
康復之路:Mark自1990年到2017年期間擔任MHA Village綜合服務機構的醫療主任,該機構是一個以康復為基礎的精神健康護理模式。他目前是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CSULB)學生健康服務與輔導中心的精神科醫生。他的臨床實踐基於超過30年的經驗,專注於為我們社區中最難接觸和最弱勢的群體提供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