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17 12:16貓頭鷹 文/摘自《瘋癲文明史:從瘋人院到精神醫學,一部2000年人類精神生活全史》
【文、圖/摘自貓頭鷹《瘋癲文明史》,作者史考爾】
其實,我們對大部分的精神疾病病因,仍然一無所知,但是賣弄這些生物學術語對於行銷藥物來說,倒是相當好用。 圖/ingimage
生物學的反噬
十九世紀晚期,全世界的精神科醫師都相信精神疾病乃是某種大腦跟身體失常的疾病。精神病患是比較低劣的人種,他們的疾病是身體正在退化的最佳例證:情緒遲鈍、思想跟言語混亂、缺少動機;或者有太多想法,對自己的行為完全無法控制,或是妄想,或是看見幻覺,或是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或是情緒低落憂鬱得不可自拔。時至二十世紀,精神醫學又再次擁抱精神疾病的生物面向,而漸漸忽略了其他面向。一九九一年美國總統老布希代表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所發出的總統公告裡,宣稱一九九○年代將是「大腦的十年」,但這公告只不過是某種形式的核可了早已流行在精神醫學界的趨勢,而這趨勢並非只限於美國。
專家會告訴病人跟家屬,精神疾病的病因來自於大腦生化機制的問題,像是缺乏多巴胺或是血清素等等。但是這其實只是用賣弄生物學術語來取代賣弄心理學術語,兩者誤導跟不科學的程度不分軒輊。其實,我們對大部分的精神疾病病因,仍然一無所知,但是賣弄這些生物學術語對於行銷藥物來說,倒是相當好用。同時,精神醫學界正受到鉅額研究經費的誘惑跟收買。在過去,精神科醫師身處於醫學中最不受重視與尊敬的幽暗角落裡,他們所謂的談話治療,以及對於兒童時期性欲的執著,只會招致主流醫學界更多的訕笑與輕視。但是現在他們卻成了醫學院的寵兒,可以獲得數以百萬美元計的研究經費,還有各種間接回扣,都助長了自二戰以來,業已蓬勃發展的醫學-產業複合體更形壯大。
大部分的經費都來自製藥業,這產業在二十世紀發展了四分之三個世紀,早已成為一個成熟的產業。大藥廠的興起,可以算是比較晚近的現象。它們都具有強大無比的行銷能力,勢力橫跨全球,可以跨越任何國界搜尋所有可能獲利的新化合物,不過卻常常退到比較邊陲的國家去進行新藥研究,因為這些地方的倫理規範比較鬆散,比較容易規避,從各醫學中心所搜集來的臨床試驗資料,也比較容易納入公司的掌控之下。這些藥廠的獲利相當驚人,遠遠超過其他的經濟活動。它們大部分都從這種利益龐大又毫無節制的醫學大混戰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其中又以美國為最大的市場,也因此讓美國精神醫學界在全球占有支配性地位。
精神藥物是大藥廠能夠擴張跟獲利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這並不是因為發明了什麼像當年的盤尼西林一樣的靈藥。相反地,所有精神藥物學所吹捧的藥丸或是配方,全都只能治標而不能治癒疾病,甚至有時候,它們連減輕症狀也做不到。不過很諷刺的一件事是,正是因為這些藥物相對薄弱的治療效果,讓它們如此有價值,很容易就可以躋身成為業界口中的暢銷藥,為藥廠帶來數十億美元的利潤。能夠治病的藥物當然相當了不起,不過這是對病人而言確實如此,對藥廠來說就不一定了。比如說抗生素,在還沒有被濫用到變得無效以前,可以輕易地治癒許多細菌感染的疾病。在一個世紀以前還嚴重到會致命的疾病,現在只要吃個藥治療就可以了。但是一旦那讓人興奮的療效出現過後,藥的銷量跟獲利就大幅萎縮,藥廠無法從這些藥獲得太多的利益。所以,可以透過藥物控制而非治癒的疾病,才是藥廠的目標,像是第一型跟第二型糖尿病、高血壓、那些會在血流中愈積愈多,塞住血管的膽固醇,或者像是關節炎、氣喘、胃食道逆流、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感染等等,這些疾病會持續好幾年,它們才是藥廠巨大利益的來源。當然,一旦專利過期,這些藥的獲利自然也會隨之降低,但是藥廠總有辦法調整劑型,重新申請另一項專利,甚至讓藥變成另一種新的處方藥。記住,病得愈久,利益愈大。
至於在精神醫學領域,因為精神疾病往往捉摸不定,有時候互相矛盾。造成它們的原因至今仍神祕難解,而大部分的疾病卻又頑固、嚴重且讓人痛苦。我們無法對它們視而不見,但是對它們卻一無所知又束手無策。一旦有一種新藥冒出來,說可以減輕這些疾病的症狀(或至少宣稱可以如此),它的市場潛在價值之龐大,不言可喻。
因此,抗精神病藥物與抗憂鬱劑往往就是這地球上所有藥物中獲利最豐厚的幾種,排在其後的則是眾多鎮靜劑。舉例來說,必治妥施貴寶公司所生產的安立復,每年的銷售額是六十億美元。禮來公司所生產的抗焦慮藥物千憂解,則在全世界有五十二億美元的銷售額。樂復得、速悅、金普薩跟理思必妥等用來治療憂鬱症或是思覺失調症的藥物,二○○五年的銷售額都在二十三億到三十一億美元之間,長期的獲利則更為可觀。抗精神病藥跟抗憂鬱劑,經常占據美國藥品銷售排行榜的前五名。根據二○一○年的統計,抗精神病藥物在全球的銷售額是兩百二十二億美元;抗憂鬱劑是兩百億美元;抗焦慮藥物是一百一十億美元;興奮劑是五十五億美元;治療失智症的藥物也是五十五億美元;而這些都還不包括許多開給躁鬱症病人的情緒穩定劑呢。
但正如那句名言所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般認為這是經濟學家傅利曼說的,其實不然),所有醫學治療也都有其副作用,就連那些療效最好的也一樣。當我們在評估近代的精神藥理革命,以及它對於精神醫學所造成的影響時,一定要謹記這一件事。激烈反對精神藥物者自然會嘲諷或否認相關的發展。然而在此同時,在精神醫學的戰場上,藥物所帶來的問題常常是相當多元且影響深遠的。這頓午餐不但不便宜,而且還相當貴,對許多消費它的人來說,所付出的代價其實相當不值得。
藥物治療對精神疾病來說,很不幸地,並不總是特別有效;而且很多時候精神科醫師口中,以及發表於科學期刊上的論文所謂的療效,其實都被誇大了。另一方面,病人若想要享有這些藥物所帶來的好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往往不是被低估,就是被刻意掩飾。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早年的精神藥理學研究,充斥著一堆設計不良的臨床實驗,經常讓實驗結果往正面的方向偏差。後來,當製藥業發展得愈來愈龐大,變得愈來愈有勢力,加上它們追求利潤的積極程度,讓許多熟知內情的人開始擔心,現在所謂的「實證精神醫學」稱之為「操弄證據的精神醫學」,或許更為貼切。

精神醫學界足足花了二十年,才終於肯承認這件事實。第一代的抗精神病藥物像是吩噻嗪,經常具有嚴重的有害副作用。有些病人會出現類似帕金森氏症的症狀,有些病人則出現持續性地坐立不安,連一分鐘都坐不住;還有一些病人則恰恰相反,會有很長一段時間一動也不想動。其中最嚴重的一種副作用,是所謂的遲發性運動不能。這種症狀在病人服藥期間往往看不見,但是病人隨後嘴唇會不自主地做出吹吸,或是咬唇的動作,四肢也會無法控制地拍打跟亂動。好笑的是,不知情的人看到他們,反而還認為這就是精神疾病的症狀。遲發性運動不能常見於長期服藥的病人身上(比例不一而足,從百分之十五到六十的病人都可能會出現),而大部分的病人一旦出現這種「醫原性」症狀(所謂醫原性,就是由醫療所造成的),幾乎就無法回復。
對許多病人來說,第一代藥物吩噻嗪確實能有效減輕他們許多症狀,不止對自己的生活改善不少,對周遭的親朋好友來說,也變得比較能忍受。但是對其他為數眾多的病人來說,第一代藥物卻一點效果也沒有。對前者來說,選擇服藥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是值得的。但是對那些沒有效果的病人來說,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然而不管是哪一群病人,都必須承受藥物帶來嚴重的副作用,讓他們變得更虛弱,更被汙名化,而且不可逆轉。
隨著精神醫學界漸漸開始承認這些藥物帶來的副作用,有些人因此稱其為「毒害人的精神醫學」,而山達基教會更是在好萊塢蓋了一座博物館,稱為「精神醫學:死亡工業博物館」(一方面也同時推銷自己那些詭異的治療法)。有些人因此就相信了這些過激的觀點。這當然也不對。若說藥物治療只有百害而無一益,也很荒謬,那等於是在否認許多業已明確的證據,只是另一種極端主義而已。但這也不是說,我們對於製藥工業,以及精神醫學界裡親製藥業的觀點,都要完全照單全收。
第一代精神藥物所建立的暢銷模式,讓隨後問世的各種精神藥物也蒙受其利。這些藥包括了眾多抗憂鬱劑,一問世就像星火燎原一樣,讓被診斷為憂鬱症的病人大幅增加,變得像是精神醫學界裡的流行感冒一樣;然後還有所謂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大概在二十年前問世,這些藥物包含了形形色色不同的化學成分,據說沒有吩噻嗪那樣令人困擾的副作用。百憂解號稱可以讓病人「比好還要更好」,但是後來發現其實並非如此;至於其他同類的抗憂鬱劑,亦即一般所稱的「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SSRI)也都不是什麼萬靈丹。這些藥物就算有其正面的效果,卻往往伴隨著更嚴重的副作用,特別是許多研究指出,用在嚴重的憂鬱症病人身上時,它們的效果比安慰劑好不到哪裡去。哈佛大學的精神醫學家海曼如此結論道:我們的處境仍然相當黯淡,雖然「自一九五○年以來,發明了許許多多的抗憂鬱劑……但其療效並未比第一代更好,因此對許多病人來說好處有限,甚至根本沒有好處」。
當SSRI被用來治療兒童時,它會大幅增加病人想自殺的念頭以及自殺比例(這項副作用長期以來一直被藥廠否認跟隱匿);揭露這件事情的,並不是精神科醫師本身,而是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調查記者。英國政府專門負責審查新療法臨床價值的機構,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原本打算核准讓SSRI用在兒童身上,但是在最後一刻打消了念頭。二○○四年他們的意見改成反對給兒童使用。隨著愈來愈多負面的臨床實驗結果被公開,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終於要求在這些藥品仿單上,加上最嚴重的「黑盒警語」來註明藥物的危險性,最後甚至讓這些藥物撤出市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同時也拒絕核准將克憂果跟樂復得之類的精神藥物,用在年輕人身上。後來又有其他調查指出,雖然在公開發表的研究結果中指出,SSRI類藥物能有效治療兒童跟青少年的憂鬱症,但是這些研究「其實都受到某些操弄,以至於負面結果都被用正面的方式呈現出來,而沒有療效的部分以及藥物的副作用,則都被隱匿」。更糟糕的則是,還有更多對SSRI類藥物不利的負面研究結果,被壓住沒有發表。若不是來自外在的壓力,這些研究結果恐將永無被攤在陽光下的一天。
「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一般俗稱為「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但是這個名稱其實有誤導之嫌,因為這些藥物中號稱最有效的一種,可致律,根本不是什麼新藥。可致律最早是在一九五八年由一間名叫「溫德」的德國公司所合成出來的(譯注:溫德早期曾製造阿華田,後來被諾華藥廠購併)。它在一九六○年代通過了一系列臨床試驗之後,於一九七一年上市。但是,後來發現它偶爾會導致一種危險(有時甚至是致命)的血液疾病:無顆粒白血球症(血液中某種白血球數量減少),結果在上市僅僅四年後,就被製造商下架。一九八九年,可致律又慢慢開始回到市場上,被用來治療那些對其他藥物沒有反應的思覺失調症病人。在嚴格的安全預防措施下使用,這種藥成了這些病人的最後一線希望。但也因此藥品價格就變得非常昂貴,山德士對此藥一年份的定價是九千美元,比較起來,一年份的氯丙嗪(托拉靈)只要一百美元。儘管如此,可致律的銷量還是大幅成長。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藥廠宣稱,此藥的副作用很少;像是遲發性運動不能之類的副作用,比起其他的抗精神病藥物來說,都要少很多。
不久之後,許許多多其他的「非典型」藥丸也一個一個冒出來了,像是理思必妥、金普薩、思樂康等等,都各自有其專利。但是這些藥品的化學成分其實差異甚大,所以全部自稱為「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只是一種高明的行銷策略,為的是貼上這個標籤就可以用「更好且更少副作用」為賣點來銷售,果不其然,每種藥的獲利都相當可觀。雖然售價很高,但是還是受到全世界精神科醫師的歡迎。沒過多久,這些藥品也被用來治療躁鬱症病人。但是十年之後,《刺胳針》期刊卻稱這些新藥為「假發明」:「這些第二代藥物跟那些典型藥物,或是第一代抗精神病藥物相比,其實都沒有什麼非典型的特性。這一群藥物既沒有比較有效,也無法改善特定症狀,跟第一代抗精神藥物比起來,副作用沒有什麼不同,成本效益也沒有比較好。」比方說,在所有這些藥品中,只有可致律沒有被指出會引起遲發性運動不能,但是創造出一個「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的分類,可以讓藥廠把所有其他藥品都歸類到這個假分類之下,以掩蓋它們並沒有和可致律相同特性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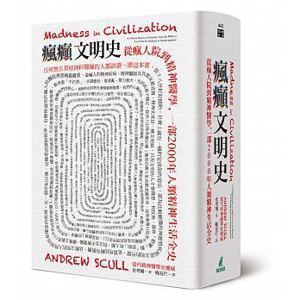
.作者:史考爾
.譯者:梅苃芢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日期:2018/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