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根狂野-2022 年 7 月 22 日
我獲得了 Orna Ophir 的《精神分裂症:未完成的歷史》(Polity,2022 年)的高級審稿人副本,因為我想看看圍繞“精神疾病”的對話,尤其是像精神分裂症這樣的污名化診斷,在心理健康專業人士之間是否發生了變化行業。Ophir 是紐約州執業的私人執業精神分析師,也是歷史學家,就她的最新著作而言,這被證明是一個令人著迷的組合。前四章充滿了對牧師、哲學家、政治家、“病人”和一般人如何與帝斯曼稱之為“精神分裂症”的一系列經歷進行鬥爭的歷史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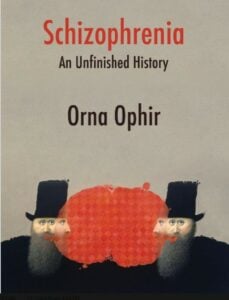
這樣的概述,特別是如果你從聖經開始,是出了名的難以完成,因為每個主題——從精神分析到宗教,再到在這種診斷的演變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每個歷史人物——都可能是一本書在其自己的。Ophir 巧妙地涵蓋了這一領域,激發了來自不同背景和學科的讀者的興趣。作為一名基督徒,我會喜歡對“精神疾病”和靈性進行更深入的探索,特別是因為當他們在同一句話中聽到宗教和“精神疾病”時,主流似乎會想到“驅魔”。Ophir 強調,許多在今天的文化中會做出診斷並接受“治療”的人實際上被認為比那些沒有經歷過我們今天所說的“症狀”的人更聰明和/或更接近上帝。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人們可以預期一個越來越世俗的社會會摒棄“過分”的精神概念,但即使是現代基督教也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這樣一種觀念,即某人會被診斷出帶有帝斯曼標籤在聖經時代,今天可能被視為特殊的或被上帝選擇的。教會最終確實開始使用“精神疾病”作為一種妖魔化和沈默威脅他們權力的人(主要是女性)的方式,例如聖女貞德和諾里奇的朱利安,但我們的文化缺乏我們所謂的“精神疾病”的知識” 在現代是在任何一點與智慧或親近上帝有關。所以這是在 Ophir 的作品中可以找到的寶石。作為一個獲得基督教神學學位的人,也許我的工作就是將其作為考慮因素;我也會對歷史學家的觀點非常感興趣,因為教會並不存在於真空中。但我相信 Ophir 讓我意識到,在“精神疾病”方面,教會在全面接受世俗的精神健康“治療”模式方面幾乎與文化沒有區別,而且,作為一名神學家,我不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
Ophir 提供了精神分裂症的歷史,因為它出現在另一本“聖經”中,診斷聖經也稱為 DSM。她包括了塑造“診斷聖經”五個版本中的每一個的哲學,這清楚地說明了為什麼每個版本都包含和排除了它所做的各種診斷,但她對 DSM 的中立及其越來越多的人類病態化經驗表現為倡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沒有提及DSM委員會成員與製藥行業日益密切的聯繫。這讓我很好奇她為什麼根本不提這件事:她是否必須對大型製藥公司的問題保持沉默才能出版她的書?她真的不知道這些利益衝突嗎?
總的來說,這本書中關於藥物的內容很少,除其他外,它揭示了圍繞藥物的對話是多麼緊張和令人擔憂。精神藥物已經知道醫源性風險,但似乎任何時候出現與心理健康有關的藥物主題,關於不提供醫療建議和人們需要繼續按規定服用藥物等的免責聲明很快就會跟進。大型製藥公司不太可能不依賴精神分裂症的診斷,特別是因為它在美國以及許多其他西方國家銷售為終生的、無法治癒的,因此需要幾十年的藥物“管理”。然而,關於製藥行業對 DSM 的深刻影響、臨床醫生的培訓和治療技能,Ophir 很少窺視,
Ophir 確實承認在聽到聲音的人如何理解和體驗這些聲音方面存在文化差異。她引用了對聽力運動 (HVM) 主張的“激進”解釋:“如果我們傾聽,可能會聽到聲音告訴我們更多關於破碎社會的信息,而不是破碎的大腦。” Ophir 沒有進一步探索“破碎的社會”:為什麼發展中國家的聲音聽眾與他們的聲音之間的對抗性,甚至友好的關係較少,而在美國西部長大的人的聲音更有可能是暴力的,指揮暴力和責備聲音的聽眾?為什麼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聲音聽眾報告他們的聲音可以保護他們的安全,而來自西方國家的聲音聽眾卻體驗到他們的聲音告訴他們傷害或自殺?相似地,儘管 Ophir 指出,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聽力一直受到社會重視,而西方將其作為疾病的首要症狀,但她並沒有深入研究為什麼會這樣。當然,這些都是概括性的,但我們可以製作它們的事實及其原因,可以說比心理健康行業專家投票將其納入 DSM 更重要,無論他們的理念或培訓是什麼。
事實上,如果心理健康產業聯合體或其僱傭的臨床醫生真的對“治療”和“幫助”人們感興趣,他們難道不想知道為什麼美國人和西方社會的人有暴力的聲音,而被剝奪權利的世界卻更友好嗎? ,與他們建立更支持甚至挽救生命的關係,以便他們能夠開發出更有效的治療方法?雖然 Ophir 的精神分裂症診斷歷史和 DSM 在其中的作用很有趣,但在討論“精神疾病”時,文化批評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語音聽眾的體驗存在如此明顯差異的情況下。Ophir 的書在歷史方面更強大、更豐富,這很奇怪,因為 Ophir 也是一名臨床醫生,但文化與歷史密不可分。
但這帶來了一個更大的問題:臨床醫生和“患者”之間的分歧繼續存在甚至加深,儘管關於“精神疾病”的討論已經開始在文化上轉變為更容易接受,甚至更流行——僅適用於某些診斷, 當然。焦慮和抑鬱很流行,人們在 TikTok 上炫耀他們的多動症,我們認為我們正在“談論心理健康”作為一種文化。誰不在房間裡?帶有污名化標籤的人:邊緣性人格障礙、一定程度的自閉症和精神分裂症。即使在 Ophir 的書中,被貼上精神分裂症標籤的人也像在文化中一樣被邊緣化:他們的聲音大多只出現在七章每一章開頭的題詞中。即便如此,
Ophir 確實承認從“專業知識”轉變為向聽眾發聲的重要性,這已經在進行中,她將其主要歸功於聽力運動。她引用了該運動創始人的一句話,這句話準確地概括了她在書中所涵蓋的歷史,正如一句話所能做到的:“我們這些聽到聲音的人可能生活在錯誤的世紀。” 當然,主流醫學/精神病學機構聲稱 HVM 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來詆毀它。為什麼?
她將 HVM 歸功於“小心 [ing] 反對將具有獨特經歷的個人系統化醫學化的趨勢,以直接或間接地迫使他們改變為他們不是的人(即非語音聽眾),通常具有精神病學的全部重量,支持這些可疑努力的醫療甚至政治機構。” 在其典型的抹黑任何威脅其商業模式的東西的模式中,心理健康行業毫不奇怪地尚未完全認識到 HVM 的說法,即聲音聽者是完全有效的身份,完全不同於任何診斷,包括精神分裂症。
Ophir 承認 HVM 尚未“完全驗證”,但並未充分挑戰進行驗證的系統,或該系統的文化影響以及保持其到位的反饋循環:心理健康領域通過告訴我們來表明權威依賴“專家”以外的任何人都是“危險的”,這會使人們“獲得”聽起來像心理學家/臨床醫生/治療師這樣的官方頭銜,需要更高的教育和學位才能執行他們稱之為“治療”“患者”的某些任務。疾病。” 然後,反過來,主流文化質疑我們所教授的領域之外的任何“專業知識”(值得注意的是,仍然很少涉及#ownvoices,他們的經歷正在被辯論,貼上標籤,最重要的是為人們負責,用藥和貨幣化)。
Ophir 強調種族複合的方式,並加深了一般診斷的污名,特別是那些仍然被視為“危險”的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她還呼籲將診斷武器化以使持不同政見者沉默,類似於教會如何將那些挑戰其權力的人稱為“精神病患者”。她沒有說明的是帝斯曼如何越來越多地創建診斷“譜”,這有助於將越來越多的人類經歷病態化,並捕捉越來越多可能對現有權力結構構成威脅的人,將他們匯集到“待遇”並駁回他們對這些結構的合法投訴。她只是將“光譜化”疾病作為一個事實陳述,錯過了另一個機會來挑戰利用“精神疾病”來強化分裂和痛苦的結構,同時保持當前的權力結構穩固。她深入探討了各國如何改變精神分裂症的名稱;雖然承認語言很重要,但改變對話是不夠的,實際上可能適得其反。當她說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更改名稱時,她是對的,但重要的是改變人們被對待的方式——如果“對待”不僅限於心理健康產業綜合體所做的事情,而是整個社會所做的事情。改變談話是不夠的,實際上可能適得其反。當她說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更改名稱時,她是對的,但重要的是改變人們被對待的方式——如果“對待”不僅限於心理健康產業綜合體所做的事情,而是整個社會所做的事情。改變談話是不夠的,實際上可能適得其反。當她說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更改名稱時,她是對的,但重要的是改變人們被對待的方式——如果“對待”不僅限於心理健康產業綜合體所做的事情,而是整個社會所做的事情。
精神分裂症的最後幾個問題:1)沒有提到精神藥物的瘋狂毒性及其造成的傷害,以及經歷腦芯片“妄想”的人實際上可能不會經歷“妄想”。埃隆馬斯克的 Neuralink 確實想將芯片植入人的大腦,以融合人類和機器並推進超人類主義議程。只是說。2) Ophir 提倡“更好的治療”,而不是挑戰治療本身的想法。這並不奇怪,因為她是一名臨床醫生,而治療是商業模式的一部分。
總的來說,《精神分裂症》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特別是對於那些真正對與心理健康相關的歷史和哲學感興趣的人,如果你把它作為圍繞高度污名化標籤的專業對話的脈搏。每本書都有差距,因此,在閱讀時,請記住以下問題:創建這些標籤的人是誰,他們會有“正常”的量尺?誰會從 DSM-5 引導我們(或根本沒有)的方式給人類貼上標籤中受益?為什麼“正常”是一種理想的品質,即使它可以以某種方式衡量或達到?
***
Mad in America 擁有不同作家群體的博客。這些帖子旨在作為一個公共論壇,廣泛地討論精神病學及其治療。所表達的意見是作者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