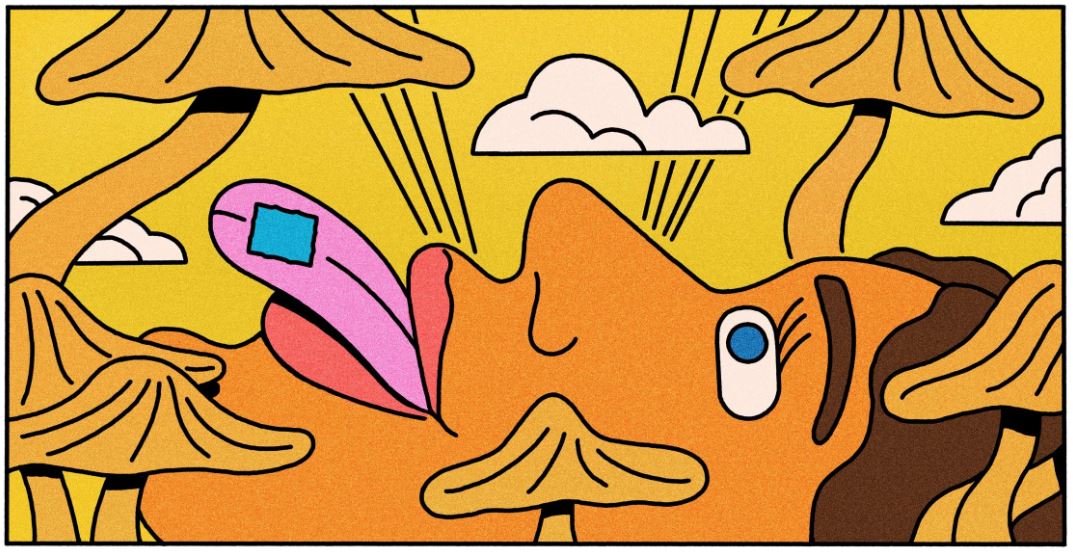關於 Timothy Leary、Michael Pollan 和 Tao Lin 的旅行報告。
艾米莉·維特2018 年 5 月 29 日
1960 年,艾倫·金斯伯格給時任哈佛教授的蒂莫西·利裡寫了一封信。利裡曾邀請詩人到劍橋參加他對新合成的化學裸蓋菇素的研究。金斯伯格熱情地回應,然後列出了他的資格:1959年LSD,作為斯坦福大學研究的課題;死藤水第二年去南美旅行;笑氣; 醚; 麥司卡林;大麻; 曼陀羅; 鴉片劑。他補充說,“嚎叫”的第二部分是“仙人掌寫作”。他解釋說,他在這一切中的動機是恢復一種失落的感覺,這是他年輕時經歷的“一系列與閱讀布萊克有關的神秘經歷”。
Leary 的生平被廣泛報導,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回憶錄中。1960 年,當他去墨西哥時,他 40 歲,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並第一次嘗試了迷幻蘑菇。他回到哈佛,向 Sandoz 下訂單,後者隨後生產 LSD 和裸蓋菇素(蘑菇中化學物質的合成版本),並與他的同事理查德阿爾珀特(現稱為 Ram Dass)開始了哈佛裸蓋菇素項目。邀請金斯伯格是利里為他的實驗招募詩人和藝術家的幾個提議之一。在金斯伯格訪問劍橋之後,他提出將 Leary 介紹給感興趣的朋友,其中包括 Grove Books 的出版商 Barney Rosset、詩人 LeRoi Jones(後來稱為 Amiri Baraka)、Muriel Rukeyser 和 Robert Lowell,
Leary 和 Ginsberg 之間的交流被收錄在一本新書《The Timothy Leary Project: Inside the Great Counterculture Experiment》中,”由檔案保管員詹妮弗·烏爾里希 (Jennifer Ulrich) 彙編,他在 2011 年紐約公共圖書館收購利裡的文件時負責管理這些文件。烏爾里希在這裡收集了金斯伯格和他的搭檔詩人彼得·奧爾洛夫斯基 (Peter Orlovsky) 的幾份旅行報告;來自傑克·凱魯亞克;來自研究生和學者;並來自利裡本人。它們是 Bluelight 和 Erowid 等互聯網論壇的原型版本,講述了奇蹟、敬畏和愛。“我正在經歷,如果不是未來的話,我們物種的進化,”一位名叫喬治·利特溫的研究生寫道,他在服用裸蓋菇素時與超凡脫俗的生物相遇。“他們是非凡的人,美麗、溫柔、優雅且充滿光明。”
“我回到家,與母親進行了第一次嚴肅的長談,持續了 3 天 3 夜,”傑克·凱魯亞克向 Leary 報告。“我知道我比我想像的更愛她。”
奧爾洛夫斯基寫道:“我們是上帝的球在他的後兜里,還是我們是上帝,我們的心腦中有這個太陽,在使用裸蓋菇素時會發出高光。” “美好的事情發生了,我想要更多。”
眾所周知,Leary 很快放棄了臨床方案,將 LSD 和裸蓋菇素分發給學生和他的朋友。Leary 和 Alpert 在 1962 年對他們最初研究的九頁摘要“自然環境中的美國人和蘑菇:初步報告”可能讀起來很有趣,但作為對另一項擬議研究的回應,Leary 的主管認為,長期“groovy”和“love Engineer”等術語並不能很好地服務於術語觀測數據。(烏爾里希包括一封哈佛教員寫給 Leary 的信,指示他不要再告訴 Sandoz 他的實驗是為學院服務的。) 1963 年,哈佛解雇了 Leary,當時他的非正式藥房引起了太多爭議。在梅隆家族繼承人的幫助下,利裡將名義上仍是研究機構的地方搬到了米爾布魯克,在紐約州北部。Ulrich 包括有關 Millbrook 的研討會和課程的文件,以及一個“體驗計劃和記錄圖表”,其中分類為“中陰”,即藏傳佛教來世的陰間——一種理論的開端,將合併為“迷幻體驗:基於西藏亡靈書的手冊,”Leary 和 Alpert 與哈佛合作者 Ralph Metzner 於 1964 年合著的書。1965 年,Leary 和 Alpert 進行巡迴演講,但直到 1966 年,在幾次觸犯法律之後,Leary 才開始贏得“LSD 吹笛者”的美譽,培養媒體,說事情比如,“要學習如何使用你的頭腦,你必須走出你的頭腦,”和“打開,收聽,然後退出”。許多人將 1970 年聯邦對迷幻藥的禁令至少部分歸咎於 Leary 在助長道德恐慌中所起的作用。
烏爾里希的選集,其中許多以前未發表過,完善了利裡的人生軌跡,從教授到大師,再到逃亡者,再到對自己的懷舊漫畫。這些文件涵蓋了 Leary 在哈佛的日子到他作為互聯網佈道者的日子,當時他的格言變成了“PC 是 19 世紀 90 年代的 LSD”。(彌賽亞宣言對他來說很容易。)烏爾里希總結說,如果李瑞“在受控的醫療監督下悄悄地在哈佛進行他的藥物研究,那麼他的故事和反主流文化的故事今天可能看起來非常不同。”
金斯伯格對他的實驗結果很滿意。他在 1961 年 1 月為 Leary 寫的旅行報告中寫道:“在我看來,psilocybin 是某種通靈的天賜之物。” 他並不是唯一一個想要重新創造神秘體驗的人。正如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在“幻覺,” 2012 年發表,“人的日常生活還不夠;我們需要超越、運輸、逃離;我們需要意義、理解和解釋;我們需要看到我們生活中的整體模式。”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 LSD、psilocybin 蘑菇、麥斯卡林、死藤水和其他化學品自 19 世紀 50 年代現代引入以來在美國文化中保留了重大影響的能力。1970 年的聯邦禁令將他們轉移到地下。但是,根據 2010 年的一項調查,儘管法律規定此類實驗為非法,但仍有約 3200 萬美國人在其一生中嘗試過 LSD、麥斯卡林或魔法蘑菇。
儘管在公立學校的 DARE 課程中我被教導要抵制所有同伴壓力,但沒有人邀請我作為高中或大學生放棄酸。作為一個生活在小石城、邁阿密和紐約的年輕人,LSD 並沒有考慮到我朋友的隨意吸毒,他們傾向於使用酒精、大麻、可卡因或共享的 Adderall 和 Xanax 處方。(兩千年初,一次重大的聯邦破產使全國供應大大減少,但我也沒有很努力地去尋找。)正如陶林在他的新書《旅行:迷幻、異化和變化》中所寫的那樣,” “我半信半疑地相信我在一生中吸收的關於迷幻藥的刻板印象——它們會導致精神錯亂和失控的行為,而且是危險的和無趣的。服用迷幻藥的人,在沒有發瘋的情況下,似乎懶散、嬉戲或在田野裡跳舞,不擔心或思考任何事情,而只是(我一直覺得有點毫無意義)看他們通常描述為幾何圖形的事物。”
在“旅行”中,林描述了他從 2012 年到 2016 年的生活,這段時間他開始刻意研究迷幻藥。小說《台北》出版後,”其中角色消耗 MDMA、Xanax、海洛因、蘑菇等,林說他在寫這些時對安非他明和其他藥物採取了“‘不惜一切代價’的態度”,他試圖從藥物轉向迷幻藥吸毒是“持續的、有意識的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不要走向無意義、抑鬱、喪失權力的辭職形式和存在主義等黯淡的意識形態”。林的第八本書是他的第一部非小說作品——混合了回憶錄、關於裸蓋菇素、DMT 和鼠尾草等物質的旅行報告,以及關於植物學、健康和人類進化的題外話。林避免用比喻性的語言寫作,這些報告中幾乎沒有誇張,也沒有提到 19 世紀 60 年代的酸性形而上學。“旅行”,如果不是自助指南的話,是一本關於一個人試圖變得更快樂的書,
這也是講師兼作家特倫斯·麥肯納的傳記,自 2000 年麥肯納去世以來,他關於 19 世紀 80 年代和 19 世紀 90 年代迷幻藥的論述一直保存在 YouTube 上。林寫道,麥肯納反對大師,並貶低他那個時代的新時代自助邪教。2013 年夏天,我在自己的迷幻藥物實驗中,在我 31 歲時第一次嘗試迷幻藥物時,在林的推薦下聽了麥肯納的講座。我在那個夏末和秋天跑步時聽了麥肯納的講座。在我看來,正如林所寫的那樣,“他比我從意識和想像等非物質主題中吸收了這麼多信息的任何人都更加認真、複雜和不迷信。
當我開始閱讀迷幻文學的經典時,我更好地理解了,與我們小學教育的宣傳和李瑞樹立的榜樣相反,一個人可以成為一個有思想的、符合現實的,甚至是職業成功的人,而且還可以LSD、psilocybin 或死藤水。我讀過的一些書是自行出版的,有編輯錯誤,或者提出了自上而下的理論,但其中大多數比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網站上的信息更具指導性和可信度。有時我覺得我發現了一段平行的文化史,就像我讀到卡洛斯·卡斯塔內達的“唐璜的教誨”中的一段時,意識到它一定影響了我最喜歡的一本兒童讀物,一部關於女巫的小說在黑暗時代,被稱為“聰明的孩子,”莫妮卡·弗隆(Monica Furlong),一位聖公會教徒,是艾倫·瓦茨的傳記作者,曾嘗試過酸。我對毒品的了解越多,在美國控制毒品的範式就越顯得不僅不公正而且不合邏輯。2013 年,我參加了在紐約市舉行的年度 Horizons 迷幻藥會議,當時已經是第七個年頭了。我去了死藤水儀式。
其中一些選擇現在看起來已經陳詞濫調,是廣泛的文化重新評估的一部分。John Misty 神父在談論蘑菇,而 Chance the Rapper 在談論 LSD;RuPaul 和 Steve Jobs 正在回憶年輕時的旅行;關於迷幻藥的醫學潛力的研究登上了《泰晤士報》的頭版;漢密爾頓·莫里斯開始記錄他的精神冒險經歷為副。從 19 世紀 90 年代形成的在線毒品極客社區中,一群組織聯合起來,致力於糾正他們認為美國毒品政策的最嚴重錯誤,包括“毒品戰爭”的失敗:DanceSafe 、藥物政策聯盟、精神實踐委員會、研究智囊團迷幻研究多學科協會和百科全書藥物網站 Erowid(我在這裡寫過)等等。這些構成了現在被稱為開明毒品運動的基礎,這是一種重新評估美國與精神活性化學品的法律、醫學、教育和社會關係的多管齊下的方法。
這一運動最有效的戰線之一是科學研究。在“如何改變你的想法:迷幻新科學教給我們的關於意識、死亡、成癮、抑鬱和超越的知識”中,邁克爾·波倫將“迷幻研究的現代復興”追溯到 2006 年,即阿爾伯特·霍夫曼 (Albert Hofmann) 的百年誕辰,誰首先合成了 LSD 和裸蓋菇素。霍夫曼還活著,那一年,他在日內瓦舉辦了一個生日派對,然後變成了一個會議,來自美國和瑞士的研究人員在政府批准的實驗的前沿開會並討論了他們的發現。同年,最高法院裁定一個宗教團體,巴西教會 União do Vegetal 的一個分支,可以合法地進口死藤水作為聖禮,這為迷幻藥物的合法化開闢了一條可能的宗教道路。
Pollan 在 2006 年發現的第三個重要事件是在《精神藥理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Psilocybin Can Occasion Mystical-type Experiences”的論文,他寫道,這是“第一個雙盲、安慰劑對照的臨床研究”。超過四個十年——如果沒有的話——來研究迷幻藥的心理影響。” 金斯伯格近 50 年前所尋求的東西現在已被“科學證明”——儘管,正如 Leary 可能所說的那樣,這項研究能揭示出數以百萬計的其他人尚未發現的東西嗎?
波倫出生於 1955 年,“在迷幻藥首次出現的十年中途”。從 19 世紀 50 年代到 60 年代中期,數以千計的實驗(其中許多是政府資助的)測試了 LSD 在治療精神分裂症、酗酒和其他心理問題方面的功效。在愛之夏,波蘭只有十二歲。“當嘗試或不嘗試 LSD 的想法湧入我的意識時,它已經完成了從精神病藥物到反文化聖禮再到摧毀年輕人思想的快速媒體弧線,”他寫道。直到 50 多歲,一篇關於迷幻藥研究的文章登上了《泰晤士報》的頭版,波倫才決定重新考慮自己的禁慾。
“如何改變主意”試圖展示迷幻藥物的可能性,但不會過度挑戰普通 NPR 聽眾的共識現實。波倫一直強調他的消息來源的學術資格和沈穩的衣櫥選擇。他為在自己的旅行報告中談論不真實的景象和情感時刻而道歉,這些報告記錄了他對蘑菇、LSD 和一種名為 5-MEO-DMT 的物質的體驗,這種物質由索諾蘭沙漠蟾蜍的毒液製成。“我需要說我知道這聽起來有多瘋狂嗎?”他在談到一次蘑菇之旅時寫道,後來,“寫這些話讓我感到尷尬;它們聽起來如此單薄,如此平庸。” 在第一次嘗試 LSD 之前,他諮詢了他的心髒病專家。(他的醫生向他保證,經典迷幻藥對心血管系統幾乎沒有影響。)
但波倫對科學的承諾也有好處。他採訪了英國神經科學家 Robin Carhart-Harris,他的研究表明,psilocybin 會抑制大腦中稱為默認模式網絡的部分的活動,Pollan 將其描述為“大腦活動交響曲的指揮”。他了解到,大腦是一個依賴於已知模式的“減少不確定性的機器”。正如波倫所寫,“當自我反省思維的凹槽加深和硬化時,自我變得霸道。這可能在抑鬱症中最為明顯,當自我打開自己並且無法控制的內省逐漸掩蓋現實時。” 正是在這裡,迷幻藥的醫學前景出現了。“通過平息默認模式網絡,”波倫推測,“這些化合物可以放鬆自我對思想機器的控制,
在美國,我們有將精神活性化學物質分成“藥物”或“藥物”的悠久傳統。波倫在倡導合法化方面猶豫不決,這揭示了一個屢次違法寫書的人未經審查的特權。他關於將蘑菇和 LSD 等迷幻藥重新歸入藥物類別的建議也可能受到質疑。對於其他受控物質,這往往會引起混淆:處方苯丙胺 Adderall 與甲基苯丙胺等“街頭毒品”之間的化學和臨床差異很小,但一種物質是給兒童開的,另一種是高度刑事定罪的。處方阿片類止痛藥和海洛因之間在習慣形成和身體影響方面的相似之處現已廣為人知,但多年來在市場營銷中一直被掩蓋。
迷幻藥還有比內省更多的東西。在他的書中,Pollan 採訪了一位名叫 Bob Jesse 的迷幻藥學者,當他提到“消遣性”吸毒時,他在作者中間打斷了。“也許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這個詞,”他告訴波倫。“通常,它被用來使體驗變得瑣碎。但為什麼?就其字面意義而言,‘娛樂’這個詞暗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人們服用迷幻劑來聽音樂、跳舞、與朋友聯繫、增強性體驗、創造和純粹的快樂。
林比波倫更仔細地研究迷幻藥如何成為非法的歷史,特別是在他描述在曼哈頓一個特別麻醉品大陪審團任職的章節中。他引用麥肯納的話:“迷幻藥是非法的因為有愛心的政府擔心你可能會跳出三層樓的窗戶。” 麥肯納說,它們是非法的,因為“它們讓你知道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錯誤的。” 確實,在我服用迷幻藥之後,我認為我對它們的了解大部分都是錯誤的。林總結說,他服用的處方藥片有更大的負面影響,並且比迷幻藥更難停止使用,而且幾乎沒有治療效果。“在我的房間裡獨自服用大劑量的 Adderall 時,我從來沒有在深情和親切地想著我的父母時抽泣,就像我對大麻和裸蓋菇素一樣,”他寫道。利裡假裝迷幻藥有能力改寫社會。事實證明這不是真的。在這三本書中,出現了另一種迷幻藥理論,這表明最神秘的啟示與世俗的主題有關:出生、死亡和身體;家人、朋友和愛。
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under-review/the-science-of-the-psychedelic-renaiss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