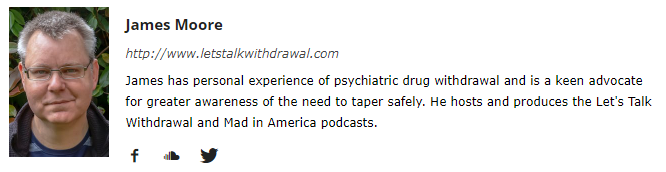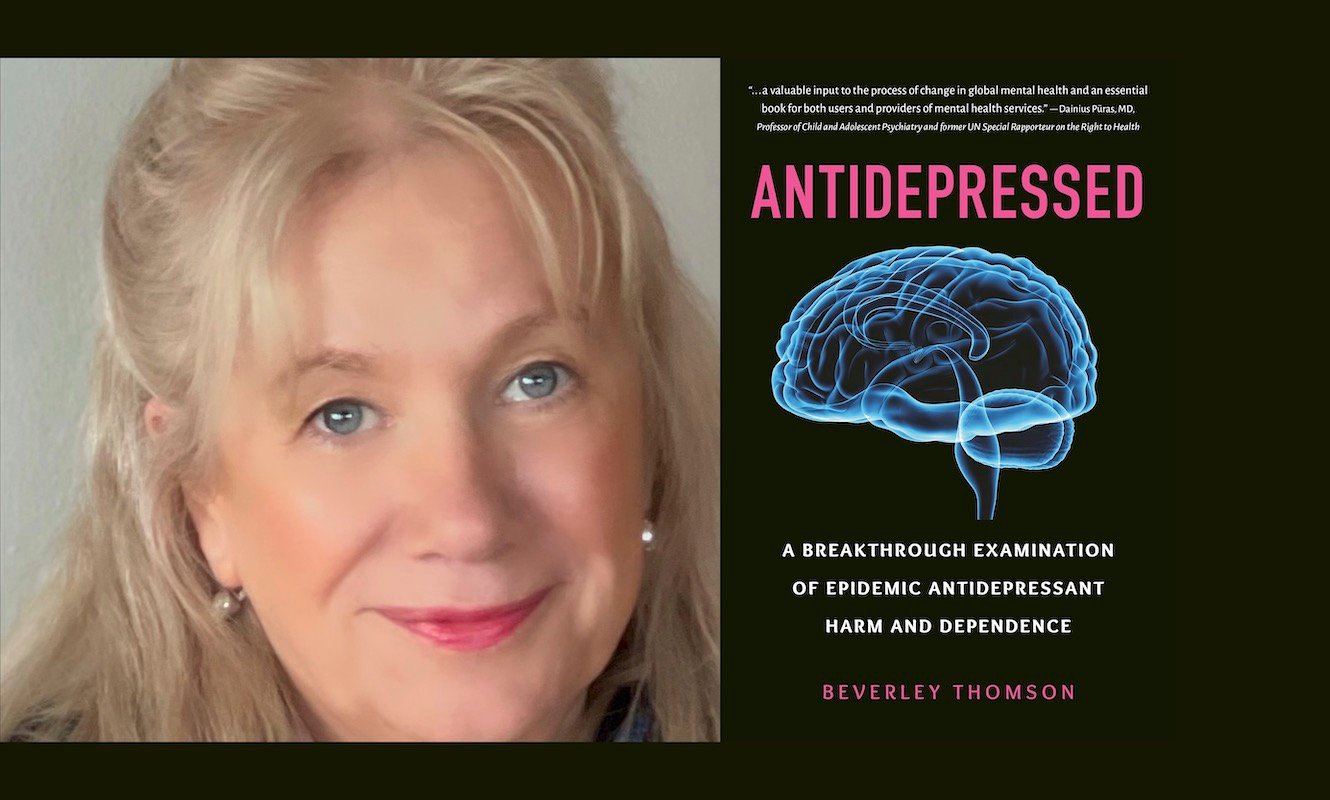詹姆斯·摩爾-2022 年 8 月 17 日
今天你的客人是貝弗利湯姆森。貝弗利是一位作家、研究員和演講者,專注於精神科藥物,包括抗抑鬱藥、苯二氮卓類藥物和多動症藥物。她對他們的歷史、藥物如何發揮作用、副作用、依賴性、戒斷和患者支持服務的發展感興趣。
在過去的 10 年中,她曾與英國醫學協會、蘇格蘭政府以及最近的英國全黨議會小組 (APPPG) 等組織合作,以解決處方藥依賴問題。她目前是蘇格蘭政府短命工作組的一員,該工作組致力於解決蘇格蘭規定的藥物傷害和依賴問題。
我們談論貝弗利的最新著作《抗抑鬱症:對流行性抗抑鬱藥危害和依賴性的突破性檢查》,由 Hatherleigh 出版社於 2022 年出版。貝弗利的著作以令人信服的敘述為特色,來自那些生活受到處方抗抑鬱藥不可挽回地傷害的人們,貝弗利的著作證明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就像一顆神奇的藥丸,假裝否則會危及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的生命和福祉。
下面的音頻已經過編輯,以保證長度和清晰度。在這裡收聽採訪的音頻。
詹姆斯摩爾:貝弗利,歡迎您,非常感謝您抽出時間加入我的 Mad in America 播客。我們很快將談論您的新書《抗抑鬱症:流行性抗抑鬱藥危害和依賴性的突破性檢查》,該書最近由 Hatherleigh 出版社出版。
但在我們到達那里之前,我想問一下你和你的背景,是什麼讓你想寫Antidepressed?
貝弗利湯姆森:非常感謝你邀請我與你交談,詹姆斯。我最初的興趣始於大約 12 年前,當時我在小學和中學擔任輔導員。我注意到老師和家長使用的語言正在發生變化,而不是問孩子發生了什麼或發生了什麼,我們開始問孩子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開始聽到“我認為他或她有問題”或“我認為他或她患有多動症”,當談到明顯難以應對學校或家庭生活或通常是複雜的社會問題的孩子時。我想我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我們開始責怪孩子們在應對通常非常具有挑戰性的環境時遇到了可以理解的困難?
這讓我開始閱讀這些問題並參加會議。我與個人談論了成人和兒童針對所謂的“心理健康問題”的標籤和藥物治療。我很快意識到這正在成為一個大問題,我對精神科藥物的各個方面產生了興趣,尤其是抗抑鬱藥,以及它們如何對人們產生負面影響。
我閱讀和聆聽的患者體驗越多,我就越知道需要聽到患者的聲音。在過去的幾年裡,我意識到需要一本以通俗易懂的方式編寫的關於抗抑鬱藥的書,其中包含迄今為止研究人員、學者和倡導者所做的所有重要工作。我的目標是寫一本書,讓我們成為抗抑鬱藥的“知情消費者”。我想寫一本不是用醫學或學術語言寫的綜合性書籍。我希望Antidepressed能夠賦予我們權力,並教育我們將自己視為這些藥物的“消費者”,而不是幾乎沒有自主權的患者。
有人曾經對我說,當你意識到事情不對勁時,你有責任告訴別人。當我開始研究時,我很早就意識到,在抗抑鬱藥和其他精神科藥物方面有很多非常錯誤的地方。
摩爾:這本書以安東尼·斯科菲爾德的一封強有力的信開頭,他在 52 歲時悲慘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從他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將自己的痛苦歸咎於服用和停用處方抗抑鬱藥。我想這個悲劇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所以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不是嗎?
湯姆森:和很多人一樣,當安東尼發現自己正遭受抗抑鬱藥的副作用和依賴時,他的生活被過度開藥和缺乏支持毀了。他的問題始於關於抗抑鬱藥負面影響的信息非常少,也沒有在線支持小組可以提供幫助。他認為他的情況歸結為缺乏專業意識,他們不承認這些藥物可能會導致這種改變生活的心理和身體傷害。直到生命的盡頭,安東尼才意識到應該歸咎於抗抑鬱藥,但不幸的是為時已晚。
安東尼去世後的兩年裡,我每週與他的媽媽布里奇特交談兩到三次,我們成了好朋友。她病重已經一年多了,但她迫切希望看到我的書出版,而她做到了,就在今年 2 月她去世之前。我失去了一個最好的朋友。
Anthony 要求他媽媽做的最後一件事是“告訴全世界抗抑鬱藥”,我希望Antidepressed能成為他們的聲音。Antidepressed不是一本關於政治或大肆抨擊藥物的書,而是關於讓我們成為 Anthony 有權成為的知情患者,而他的媽媽甚至在 80 多歲時也變得如此。對於 Anthony 和 Bridget,我希望Antidepressed能夠避免更多悲劇和浪費生命。
摩爾:我們可以先談談處方率嗎?正如您在書中提到的,我們看到世界許多地方抗抑鬱藥的處方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這僅僅是因為更多的人遇到了心理健康問題,還是有更多的原因?
湯姆森: 儘管處方量空前增加,但從未有任何證據表明所談論的“抑鬱症流行”。然而,我們在西方世界確實存在心理健康偽流行病。抗抑鬱藥處方的增加是一種文化和醫學趨勢,反映了日常生活的“醫學化”。
我們現在聽到的持續不斷的心理健康信息似乎是媒體和政治的痴迷。這些信息最終導致了抗抑鬱藥處方的增加,因為我們被告知要尋求幫助,但對於大多數這樣做的人來說,幫助將是藥物治療。政府和行業已經充分利用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相信並接受抗抑鬱藥是解決我們問題的安全有效的方法。
我們被告知我們的心理健康應該與我們的身體健康相提並論,但是當權者是否有策略地利用這些信息來逃避責任?
製藥業、精神病學和醫生得到政府、心理健康組織和慈善機構的支持,以促進“心理健康”,這意味著它已成為一個龐大的行業。我想問題是,我們是否允許或允許政府不承認和解決影響我們生活的讓我們不快樂或焦慮的社會決定因素?我們是否允許他們讓我們相信這都是我們的錯,而不是他們的錯,而我們有責任通過吃藥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我們被告知我們的心理健康應該與我們的身體健康相提並論,但我們生活在貧困、無家可歸、失業、孤獨和許多其他導致我們痛苦的社會因素中。儘管如此,我們被告知這是關於我們的“心理健康”,“我們”需要修復它。我們的社會問題已成為醫療問題,抗抑鬱藥使負責人的生活更輕鬆,但不幸的是,隨著處方率的飆升和市場的擴大,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痛苦是由這些強大的精神活性抗抑鬱藥的不良影響,往往改變生活造成的.
我想還有另一方面,當談到不斷增加的精神藥物處方時,我們作為消費者日益增長的力量似乎並不相關。雖然我們有辦法通過使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提問,但我們大多數人仍然接受我們開出的藥物是有益的,不會對我們造成傷害。
我們生活在消費者時代,在這個時代,我們可以訪問大量有關產品的信息,並且可以授權我們做出決定。在大多數商業領域,影響力和權力的平衡已經從製造商轉移到了消費者身上。事實上,在醫療保健的許多領域,醫療保健消費主義的興起和醫療保健信息獲取的增加改善了患者的選擇。
我開始問自己為什麼抗抑鬱藥和其他精神健康藥物沒有發生這種情況。當談到我們的心理健康治療時,為什麼人們會接受“醫生仍然最了解”?為什麼我們不覺得有必要讓自己了解什麼是強大且經常改變生活的藥物?
我想答案是製藥商的營銷部門不必調整他們的信息和營銷策略來滿足更知情的消費者在抗抑鬱藥方面的需求。這些信息與 1990 年代初期非常相似。我們的化學物質失衡需要糾正。
通常,現代消費者通常會事先研究他們打算購買的產品,這意味著服務提供者必須對產品有更多的了解,並在與客戶打交道時更加了解,以確保客戶滿意度。精神科藥物沒有發生這種情況。處方者不必對最新的研究有更多的了解。
處方率正在增加,因為我們允許心理健康醫學治療模式在沒有太多質疑的情況下佔據主導地位。我希望倫敦大學學院研究人員最近進行的全面審查將意味著更多的人將開始質疑“化學失衡”,人們將變得更有知識,這意味著處方者也需要變得更有知識。
摩爾:你在書中有一個部分消除了神話,你問“誰在照顧病人的利益?” 當你問這個問題時,你發現了什麼?
Thomson:自 1988 年和百憂解誕生以來,我們一直被製藥行業強大的營銷信息洗腦。在 1990 年代,全國性的運動向醫生和公眾宣傳了抑鬱症的危險,而抗抑鬱藥是簡單的“快速解決方案”。我們被製藥業和醫生說服,抑鬱症是一種生物疾病。化學失衡需要平衡,我們所有的生活問題都可以通過藥物治愈。這不必改變,因為沒有足夠多的人質疑它。
但是,如果我們將無法應對生活視為一種疾病或狀況,那麼藥品監管機構和製藥行業就會將我們視為客戶。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的是,美國的 FDA(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和英國的 MHRA(藥品和保健品監管機構)從製藥行業獲得了大量資金,並且他們在關鍵領導職位上聘用了前行業專業人士. FDA 被指控沒有將美國人民放在首位,因為他們與製藥公司有著巨大的財務聯繫。MHRA 被指控腐敗,他們承認他們為監管藥品而產生的費用完全由製藥公司的費用支付。
據說這些利益衝突導致寬鬆的法規將製藥公司的利益置於患者保護之上。大多數人驚訝地發現,FDA 和 MHRA 只需要兩次陽性試驗就可以批准一種精神藥物供公眾使用,而他們只是忽略了所有的陰性試驗。他們有操縱研究以突出積極成果的歷史。大多數精神藥物試驗當然是由製藥行業進行和委託進行的。
2019 年 3 月,FDA 非常迅速地批准了抗抑鬱藥 esketamine,以 Spravato 銷售。這是基於氯胺酮,氯胺酮會產生迷幻和認知副作用。令人擔憂的是,FDA 降低了標準並批准了此類抗抑鬱藥,據說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令人難以置信”。我們必須捫心自問“FDA 是否將患者置於危險之中,而不是將美國人民放在首位”?
摩爾:眾所周知,抗抑鬱藥會產生一系列副作用。其中更嚴重的影響可能是自殺念頭或行動的風險,有時是由無法忍受的經歷如靜坐不能引發的。我們對抗抑鬱藥治療與自殺風險之間的關係了解多少?
湯姆森:不幸的是,我們選擇服用抗抑鬱藥,因為其益處已被廣泛宣傳而風險被低估了。有共同的經歷,但每個人對抗抑鬱藥都有獨特的反應,沒有人能預測一個人會在生理和心理上對它們做出怎樣的反應。
當我們第一次服用抗抑鬱藥時,醫生很少警告我們副作用。 醫生在開抗抑鬱藥時應始終向我們提供全面的信息,使我們能夠給予充分知情同意。知情同意意味著我們了解提供治療的原因並了解益處和風險。這是我們的醫療權利,這發生在所有其他醫學領域。“化學不平衡”理論一直是處方者製造同意的絕佳方式。我的意思是相信“化學不平衡”理論意味著我們認為我們對這些藥物以及他們應該做什麼來同意服用它們並認為我們需要它們足夠了解。
SSRI 藥物的患者信息傳單 (PIL) 包含大約 200 種副作用;他們說50個很常見,140個不常見。這些不是“副作用”,而是不利影響。問題在於,患者的不良反應經歷與製藥業和醫學界所描繪的完全不同。令人擔憂的是,依賴性被列為“罕見”的副作用。
從軼事證據中,我們知道更嚴重的風險可能包括各種和不可預測的身體和精神狀態,感覺情緒麻木,感覺超然,夢想扭曲,變得激動和自殺。人們可能有嚴重的中樞神經系統問題,並且會出現複雜的神經系統影響,包括慢性腦損傷。
我稱靜坐不能是抗抑鬱藥副作用的“一個詞”。這是一種藥物誘發的狀態,當患者開始、停止、改變劑量或更換某些處方藥(包括抗抑鬱藥)的仿製藥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還知道,5% 到 10% 的人難以代謝抗抑鬱藥,這可能會在開始服藥時導致靜坐不能。
人們稱靜坐不能是失去理智的縮影。它會導致內心的混亂、無法控制的身體不安、激動和妄想症。我的書中有很多關於靜坐不能的信息,由Akathisia 教育和研究聯盟和紀念 Stewart Dolin的藥物性自殺預防和教育基金會(MISSD) 提供。
它可能導致自殺,因為像安東尼一樣,我們無法應對靜坐不能帶來的無法忍受的身體和心理影響,或者我們的思想變得如此不平衡和脫離現實,我們實際上別無選擇,只能屈服並按照我們的想法行事的自殺。靜坐不能與精神病混淆,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來了解靜坐不能被報告為首發精神病的頻率。
我們必須要問的問題是,“如果抗抑鬱藥是安全的,為什麼美國 FDA 會針對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年輕人的自殺風險發出黑匣子警告?” 自殺率上升與抗抑鬱藥處方之間似乎存在令人擔憂的聯繫。25 歲以下的抑鬱症患者使用抗抑鬱藥與自殺念頭和行為的風險增加一倍有關。所有的自殺預防策略都需要包括對處方藥引起的自殺的認識,但不幸的是,這並沒有發生。
摩爾:我們能否談談醫學上無法解釋的症狀(MUS)以及它們與抗抑鬱藥的戒斷作用有何關係?
湯姆森:醫生經常無法識別或相信身體或心理症狀是抗抑鬱藥的副作用,他們尋找其他解釋。這可能會導致檢查、測試和調查結果為陰性。然後,醫生會將患者的不良反應標記為醫學上無法解釋的軀體或功能症狀,這意味著它們的病因不明或原因不明。
然後這些可能導致診斷,例如慢性疲勞綜合症、纖維肌痛、ME 或 IBS。這正成為一個快速發展的研究領域,因為專業人士和製藥公司都在利用抗抑鬱藥帶來的不利影響。我稱之為機會主義醫學。
據估計,在英國看全科醫生的人中有四分之一患有“MUS”,看神經科醫生的人中有三分之一。醫生對看到有功能或軀體症狀的患者感到非常沮喪。這些正在成為衛生資源日益增長的負擔,患者經常受到指責並進一步接受治療。最終,它會導致更多的標籤、更多的藥物和更多的疾病。
摩爾:我想問你關於仿製藥的問題。聽眾可能知道許多抗抑鬱藥不再獲得原始製造商的專利,因此可以在其他地方獲得許可,以更便宜的價格生產。許多人可能認為更容易獲得這些藥物是一件好事,但仿製藥的製造也有隱藏的一面,你能告訴我們嗎?
Thomson:一旦品牌藥的專利到期,就可以生產仿製藥。製造商向 FDA 或 MHRA 提交 ANDA(縮寫新藥申請)以批准上市該藥物的仿製藥。例如,通用舍曲林可以在 2006 年 6 月品牌名稱 Zoloft 的專利到期時生產。仿製藥的成本比品牌藥低 20% 到 90%。
問題是我們被告知這些藥物是相同的,但它們只是在相似性上獲得批准,沒有臨床試驗,它們也不相同。仿製藥製造商實際上看不到品牌藥註冊文件。這就是製造品牌藥物的確切配方,因此仿製藥製造商開發了自己的配方。製造質量引起了人們的嚴重關注。每次我們可能會收到具有不同質量或生物等效性的不同品牌的仿製藥。
另一個主要問題是在中國生產的活性成分被製造商使用而沒有聲明原產地。所以所有的藥物都有一個API(活性藥物成分),抗抑鬱藥的質量取決於API的質量。
我們經常聽到它們效果不佳,但在精神藥物方面可能比這更嚴重。如果我們收到的仿製藥具有不同的生物等效性(例如 80% 或 110%),這可能會導致不利影響,甚至可能導致非自願退出。由於服用了不同的仿製藥,我什至收到過靜坐不能和自殺的報告。每次更換製造商時,我們可能會服用更高或更低的劑量。當保持準確的劑量至關重要時,它也可能在逐漸變細的過程中引起真正的問題。
如果我們從不同的製造商那裡獲得了一種藥物並且我們出現了不良症狀,我們需要假設這是藥物的錯。我們需要記下製造商並通知我們的開藥者。
摩爾:這本書的後半部分講述了受依賴和退縮影響的人的見證,讀到這些痛苦令人心痛。據我了解,這些證詞中的許多都支持呼籲蘇格蘭政府採取更多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我是一個短命工作組的一員,該工作組的成立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但它一直沒有效果。現在,四年過去了,發起請願書,要求蘇格蘭政府承認和支持那些受到處方藥傷害或依賴處方藥的人的 Marion Brown 剛剛收到了最終報告。2019-2020 年期間,蘇格蘭共有 967,220 人服用了抗抑鬱藥。
上週我參加了蘇格蘭今晚的新聞和文化節目,我在談論蘇格蘭抗抑鬱藥處方的驚人比率,尤其是在年輕人中。2019-2020 年這些令人震驚的年輕人開藥率可能告訴你蘇格蘭政府缺乏回應。
2019-2020 年,蘇格蘭共有 20,825 名 19 歲以下的年輕人服用了抗抑鬱藥。這在 10 年內增長了近 80%。目前的指導方針規定,只能向年輕人提供抗抑鬱藥和談話療法,在這個電視節目中,一位領先的精神病學家說:“遵循這些指導方針,不給年輕人開抗抑鬱藥作為治療的第一選擇,並給予經常監測和審查。”
我們從軼事證據中得知,這與正在發生的事情相去甚遠,我們需要質疑抗抑鬱藥與年輕人自殺和自殘之間的驚人聯繫。
摩爾:讀這本書很難不得出結論,最好的辦法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用最低劑量的任何特定抗抑鬱藥治療盡可能少的人,注意在短期治療期結束時逐漸減量. 然而,這不是我們採取的方法。似乎有越來越多的人長期服用藥物,為什麼長期服用會成為問題?
湯姆森:很多人說抗抑鬱藥挽救了他們的生命,沒有它們他們就無法生存,對許多人來說,這已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當我們可能會出現頭暈、腦震盪和疾病時,漏服一劑可能是我們依賴的第一個跡象。沒有人知道依賴抗抑鬱藥需要多長時間,但軼事證據告訴我們,對某些人來說,這並不長。這是我們應該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服用抗抑鬱藥的主要原因之一。
可能是依賴導致難以戒除抗抑鬱藥。我們的依賴程度可能決定了我們戒斷症狀的嚴重程度。如果我們試圖停止並且我們出現戒斷症狀,許多人仍然幸福地無知依賴,因為他們認為或被告知他們有復發並且他們需要藥物。數百萬人沒有意識到依賴可能給他們帶來的問題。
長期服用抗抑鬱藥和由此產生的依賴使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容易受到傷害。想像一下,您依賴抗抑鬱藥,而您無法獲得它們,無法獲得它們或傳達您對它們的需求。你新的抗抑鬱藥維持的平衡狀態可能會變得不平衡,你可能會不自覺地退出。在某些情況下,獲得我們需要的藥物實際上可能是生與死的區別。如果我們沒有適當地了解我們的藥物,並且如果我們從醫生那裡得到不好的建議,我們就會很脆弱。
如果沒有支持並且無法做出決定或正確傳達他們對藥物的需求,老年人可能會變得脆弱。當一個年輕人離開家和家人的安全時,他們可能會很脆弱,特別是如果他們沒有接受過關於突然停止使用抗抑鬱藥的危險和潛在依賴的教育。
如果我們買不起長期藥物,我們就會很脆弱。據估計,美國有 2.5 到 500 萬人正在努力負擔他們所依賴的精神科藥物。當藥物短缺和廉價仿製藥的變化造成不利影響時,我們很脆弱。
我認為我們需要從對患者和醫療行業的教育開始。我們需要更大的透明度和獲得公正研究的機會。每個人都有權服用抗抑鬱藥,但他們也有權了解潛在的危害和風險。問題是,由於全世界有數百萬人依賴這些藥物,在不久的將來要擁有一個沒有它們的世界是不可能和不切實際的。
政府和醫療保健組織告訴我們,我們應該通過了解消費者來掌控我們的健康,我希望未來人們會對抗抑鬱藥有更好的了解,他們會向開處方的人詢問更具體的治療問題。最終,消息靈通的消費者意味著我們需要有消息靈通的專業人士。
許多人變得更加了解並詢問這些藥物是否安全、有效和值得擁有,但大多數人仍然相信我們生活在一個“醫生最了解”的時代,而現實情況是,很多時候“醫生只是按照他或她被告知。”
在心理健康的許多領域,我們都在談論改變敘事的必要性。最受歡迎的問題是“你怎麼了?” 而不是“你怎麼了?” 但也許我們也應該考慮改變我們看待自己的方式。是的,我們是開藥和服藥的醫生和病人,但我們必須永遠記住,這是關於銷售和消費的。
我從我的書中引用了一段話,它解釋了我如何看待與使用抗抑鬱藥有關的未來。
在世界各國政府爭論不休的同時,醫務人員仍然故意失明,慈善機構為其提供資金,但變革必須從我們作為個人、倡導者和知情患者開始。事實上,我們知道醫生的預約通常是終生旅程的開始,因為精神病患者患有可恥的終生狀況並依賴精神科藥物,這意味著這種轉變始於我們質疑抗抑鬱藥的過度使用並尋找支持和護理的替代方法對於彼此。首先要變得更有知識,重新獲得對我們自己的醫療保健的一些控制權和權力,並承擔起盡我們所能教育自己的責任。首先要了解抗抑鬱藥不是其製造商和醫生所說的簡單快速的解決方案。
摩爾:您認為我們是否需要批判性地檢查和改變精神藥物在應對心理健康困難時的地位?
湯姆森:如果我們要避免過度使用抗抑鬱藥造成的傷害和死亡,我們迫切需要一些東西。我們需要能夠就這些藥物給予知情同意。不是我之前描述的製造同意。如果我們同意服用抗抑鬱藥,我們需要充分了解其益處和風險。
我們需要基於證據的更新處方指南,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多獨立的、非行業資助的研究。如果我們選擇服用抗抑鬱藥,我們需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服用,以避免產生依賴。
如果我們在開始、減少或停止使用抗抑鬱藥後出現症狀,我們必須始終假設這是藥物的錯,直到證明並非如此。我們迫切需要更多公正的研究,特別是關於長期影響和停用抗抑鬱藥的最佳方法。
詹姆斯,我們需要研究以較小劑量生產藥物並使用您通過請願書支持的錐形條的製藥公司。我們需要對公眾和專業人士進行教育,尤其是關於戒斷、靜坐不能和抗抑鬱藥引起的自殺。
我們迫切需要為那些受到傷害或依賴的人提供支持服務,我們必須制定撤藥和解藥計劃。非常不幸的是,英國政府最近決定不資助一條幫助許多人擺脫抗抑鬱藥的幫助熱線。
我們需要質疑對兒童、年輕人、老年人、武裝部隊和退伍軍人經常不必要和危險的處方。我們還必須質疑使用廉價通用抗抑鬱藥的潛在有害影響,因為這是一個大問題。
我並不是說人們不應該服用抗抑鬱藥,我說我們需要了解益處和風險。很多人在意識到自己依賴抗抑鬱藥時對我說“我應該知道這些事情”。我認識很多人,他們希望自己在吞下第一顆藥丸之前就已經充分意識到服用抗抑鬱藥的生活現實。我敦促人們挑戰我們對抗抑鬱藥的先入為主的社會觀念和信念。我們應該盡我們的能力教育自己,並從他人的經驗中學習。
摩爾:貝弗利,謝謝你今天加入我。對於任何服用藥物的人、任何考慮服用藥物的人、家庭成員和照顧者來說,《抗抑鬱藥》都是一本至關重要的讀物,對於任何與開藥有關的人來說尤其重要。
我不禁想到,如果他們從頭到尾閱讀抗抑鬱藥,我們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開這些藥,我們會更加小心,以確保人們不會長期服用這些藥物信息或支持。
湯姆森:謝謝你,詹姆斯。
書籍下載:
https://zh.b-ok.global/book/18629468/78a0ed
詹姆斯·摩爾 http://www.letstalkwithdrawal.com詹姆斯有精神科藥物戒斷的個人經驗,並且熱衷於提高對安全減量需要的認識。他主持並製作了 Let’s Talk Withdrawal 和 Mad in America 播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