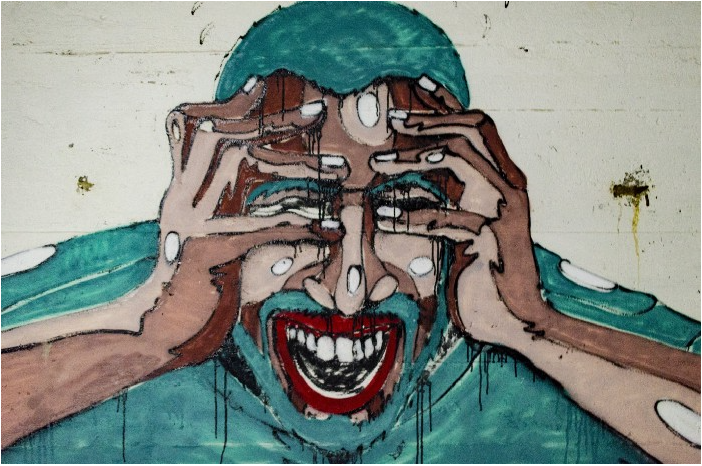2022 年 6 月 13 日
來自Medium/Markham Heid:“沒有什麼比公開羞辱更能讓人記住的了。即使是 20 年後的現在,我仍能清晰地回憶起那天我嘗試在高中同學面前彈吉他時的尷尬——但最終失敗了。
那是我大三的時候。我和幾個朋友在我們的西方文明課上做演講,我的角色包括演奏齊柏林飛艇的“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的介紹——我已經掌握並在家演奏了無數次的即興演奏。但是在一個安靜的教室裡表演,由我的老師和兩打同學看著,對我來說太過分了。我的手在顫抖,我的手指被抓住了。我“玩”了一些無法辨認的糊狀物,把消火栓變成了紅色。
每次我必須出現在觀眾面前時,我仍然會想起那一天,幸運的是,這種情況並不常見。我在練習中有所進步,但公開演講仍然讓我流汗並擾亂我的睡眠。直到最近我才知道,令我驚訝的是,我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根據最新的《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又名 DSM-5,精神衛生專業人員用來識別和診斷“疾病”),我符合社交焦慮症 (SAD)的所有主要標準。我經歷了一種“對一種或多種情況的明顯恐懼”,在這種情況下,我會受到他人的審查。DSM-5 明確包括該組中的“表現情況”,處方藥(主要是 SSRIs)被認為 是我病情的一線治療。
我沒有輕視怯場;我直接知道它有多粗糙。但我很難理解它包含 DSM。 研究人員發現,三分之一的普通人在觀眾面前講話時會感到“過度焦慮”。一些調查發現,對公開演講的恐懼甚至比對死亡的恐懼更為普遍,進化心理學家提出,這種恐懼是如此古老和普遍,以至於它一定對我們的物種有用。如此平凡而自然的人類體驗怎麼會是一種疾病呢?
一些專家說不是。他們認為,將怯場標記為障礙是更廣泛運動的一個例子,該運動將任何和所有不愉快或不舒服的感覺(害羞、悲傷、擔心、恐懼, 甚至悲傷)分流到疾病類別中。一些學者認為,這種“社會精神病化”正在導致過度診斷和過度治療,而這種趨勢部分是由製藥業設計和資助的,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現在很多人都在苦苦掙扎。我認為值得一問,給他們貼上‘精神錯亂’的標籤並給他們用藥是幫助他們變得更好的最好方法。”
文章→
https://medium.com/@mheidj/how-drugmakers-influence-our-beliefs-about-mental-illness-1570dabc7bba

製藥商如何影響我們對精神疾病的信念
一些“提高認識”活動和其他藥品營銷策略的缺點。
任何事情都會像公開羞辱一樣在記憶中燃燒。即使是 20 年後的現在,我仍能清晰地回憶起那天我嘗試在高中同學面前彈吉他時的尷尬——但最終失敗了。
那是我大三的時候。我和幾個朋友在我們的西方文明課上做演講,我的角色包括演奏齊柏林飛艇的“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的介紹——我已經掌握並在家裡演奏了無數次的即興演奏。但是在一個安靜的教室裡表演,由我的老師和兩打同學看著,對我來說太過分了。我的手在顫抖,我的手指被抓住了。我“玩”了一些無法辨認的糊狀物,把消火栓變成了紅色。
每次我必須出現在觀眾面前時,我仍然會想起那一天,幸運的是,這種情況並不常見。我在練習中有所進步,但公開演講仍然讓我流汗並擾亂我的睡眠。直到最近我才知道,令我驚訝的是,我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根據最新的《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又名 DSM-5,精神衛生專業人員用來識別和診斷疾病),我符合社交焦慮症 (SAD)的所有主要標準。我經歷了一種“對一種或多種情況的明顯恐懼”,我會受到他人的審查。DSM-5 明確包括該組中的“表現情況”,處方藥(主要是 SSRIs)被認為是我病情的一線治療。
我沒有輕視怯場;我直接知道它有多粗糙。但我很難理解它包含 DSM。研究人員發現,三分之一的普通人在觀眾面前講話時會感到“過度焦慮”。一些調查發現,對公開演講的恐懼甚至比對死亡的恐懼更為普遍,進化心理學家提出,這種恐懼是如此古老和普遍,以至於它一定對我們的物種有用。如此平凡而自然的人類體驗怎麼會是一種疾病呢?
一些專家說不是。他們認為,將怯場標記為障礙是更廣泛運動的一個例子,該運動將任何和所有不愉快或不舒服的感覺(害羞、悲傷、擔心、恐懼,甚至悲傷)分流到疾病類別中。一些學者認為,這種“社會精神病化”正在導致過度診斷和過度治療,而這種趨勢部分是由製藥業設計和資助的,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現在很多人都在苦苦掙扎。我認為值得一問是否將他們標記為“無序”並給他們藥物是幫助他們變得更好的最佳方式。
為了避免被貼上無序標籤,情感體驗必須有多可預測和普遍?將不斷擴大的經驗範圍定義為“疾病”會產生什麼後果,從而成為藥物治療的候選者?
這些都是複雜的問題,有著微妙的答案。但不可否認的是,大量美國公眾現在正在為不久前被認為處於“正常”範圍內的疾病服用處方藥。同樣不可否認的是,製藥商花費數十億美元來塑造和促進我們對這些疾病的理解。
喬治城大學藥理學和生理學教授、醫學博士 Adriane Fugh-Berman 說:“製藥公司將一種常見症狀轉化為一種疾病,以便為特定藥物打造品牌,這已變得相當普遍。”
在閱讀Fugh-Berman 的一些作品之前,我對“條件品牌”一詞並不熟悉。簡而言之,這種策略涉及營銷一種疾病以銷售更多的治療方法。例如,製藥商可能會為高速公路廣告牌付費,該廣告牌突出了其作為主要藥物治療的精神疾病的負擔。(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沒有提到製藥商及其產品。)
“不幸的是,製藥公司控制著醫生擁有的每一個信息來源。”
一個有據可查的條件品牌示例涉及社交焦慮症和葛蘭素史克製造的藥物 Paxil。
社交焦慮症在 1980 年代首次出現在 DSM 中——引起了一些爭議。在 FDA 批准藥物帕羅西汀 (Paxil) 用於治療社交焦慮症之後——通過擴大 DSM 的診斷標準使之成為可能——葛蘭素史克在 2000 年花費了超過 9200 萬美元向治療師和公眾推銷 SAD。這是根據西北大學教授克里斯托弗·萊恩 (Christopher Lane) 博士的工作得出的,他撰寫了大量(包括在他的獲獎著作《害羞》中)關於 DSM 的擴展和普通情感體驗的“醫學化”的文章。
葛蘭素史克針對 SAD 的營銷活動以標語為“想像對人過敏”的廣告為中心。Lane寫道:“[The] 競選活動沒有提到 Paxil——它不需要,因為它是當時唯一批准用於治療這種疾病的藥物。” 許多廣告本身甚至沒有提到葛蘭素史克。相反,他們引用了葛蘭素史克幫助資助的美國焦慮症協會等組織。2001 年,也就是葛蘭素史克發起這項運動的第二年,醫生為 Paxil 開了 2500 萬張新處方。所有這些過去和現在都是合法的。
除了投放此類廣告外,製藥公司還向為其進行此類促銷的宣傳團體提供財務支持。
上個月,任何花時間上網的人都一定會聽到,是心理健康意識月。Mental Health America 是第一個發起心理健康意識月的非營利組織,從製藥公司獲得資金;2020 年,其“白金”捐贈者名單包括輝瑞、百時美施貴寶和強生的製藥子公司等製藥商。全國精神疾病聯盟 (NAMI) 是美國最大的心理健康非營利組織之一,也是心理健康宣傳月最響亮的擴音器之一。2000 年代中期的一項國會調查發現,其四分之三的資金來自製藥公司。
在這篇文章中,我採訪了一位研究條件品牌並為製藥商提供有償諮詢工作的市場營銷教授。他要求我不要把他的名字寫在這裡。“你不能銷售沒有問題的產品,”他告訴我。“條件品牌識別並定義問題。”
根據他提供給我的數據,製藥公司去年在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廣告上花費了大約 70 億美元。他說,在總支出中,超過 8% 用於“疾病意識”活動和其他無品牌廣告,即未提及藥物的廣告。
我們如何解釋我們的感受——以及這種解釋有多少讓我們痛苦並塑造了我們的自我形象——部分取決於社會告訴我們要思考我們的經歷。
製藥公司還花費數十億美元來確保衛生當局和醫療專業人員能夠識別新疾病並將其與特定的藥物治療聯繫起來。Fugh-Berman 說他們可以通過許多不同(和合法)的方式做到這一點:他們可以資助有利的研究;他們可以舉辦豪華的醫學會議,由“關鍵意見領袖”(付費醫生)發表演講來支持他們的敘述;他們可以為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製作繼續教育材料,強調疾病的普遍性和嚴重性;他們可以向教學醫院或非營利性倡導團體捐款。
“不幸的是,製藥公司控制著醫生擁有的每一個信息來源,”她說。“即使是不參加行業資助活動的醫生,仍然受到行業資助信息的影響。”
根據目前的診斷標準,SAD 將影響多達 30% 的美國人在其一生中的某個時間點。多達 20% 的年輕人會出現社交焦慮或相關恐懼症,發病年齡中位數 為 11 歲。這是根據美國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學學會2020 年的一份指南文件得出的。
並非總是如此。
當我與西北大學的 Lane 交談時,他告訴我,直到 1980 年代,SAD(最初被稱為社交恐懼症)才被正式承認為一種疾病。當它確實進行了疾病分類時,它最初是嚴格定義的,因此它只包含一小部分人群。但隨後,在其 1987 年修訂版中,帝斯曼“徹底調整”了其對 SAD 的定義,使更多、更多的人符合其診斷標準。一夜之間,患有 SAD 的人數“從人口的 1-2% 上升到接近五分之一的人,”萊恩告訴我。
去年,《柳葉刀精神病學》雜誌的一項研究指出,儘管人們一直不清楚這些藥物對年輕人心理和神經認知發展的長期影響,但越來越多的青少年正在服用處方藥(主要是 SSRIs)來治療 SAD 和其他疾病。 .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在社交場合經歷嚴重焦慮的人受益於公眾對其挑戰的認識提高,也許還受益於藥物治療的改善。與我交談的營銷學教授說,他認為藥物條件品牌化做法的好處大於過度治療或過度診斷的危害。他告訴我,更多需要這些藥物的人能夠得到它們,診斷標準的擴大意味著保險公司將為更廣泛的患者群體支付治療費用。
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情感體驗總是具有暗示性的。我們如何解釋我們的感受——以及這種解釋有多少讓我們痛苦並塑造了我們的自我形象——部分取決於社會告訴我們要思考我們的感受。
將常見的恐懼、焦慮或其他具有挑戰性的情緒標記為“疾病”或“障礙”,可以通過確認一個人正在經歷的事情來提供一些安慰——通過承認,是的,你正在處理的事情是真實而困難的。但這種驗證可能會產生成本,包括處方精神科藥物的風險,所有這些都可能導致嚴重的不良反應,並且可能不會促進長期的心理健康益處或改善結果。承認一個人的痛苦並給予他們支持而不稱他們為“無序”是可能的。
換句話說,標籤很重要——尤其是當被分配標籤意味著被開藥時。
“讓人們覺得他們正常的進食、睡眠或感覺異常對他們沒有幫助,”Fugh-Berman 說。“當人們以非藥物方式更好地處理他們所經歷的事情時,它會引導人們接受藥物治療。”
更多來自馬克姆海德
我寫關於健康、科學和心理學的文章。我的作品曾出現在《時代》雜誌、《紐約時報》、《Vice》和其他地方。我住在德國。